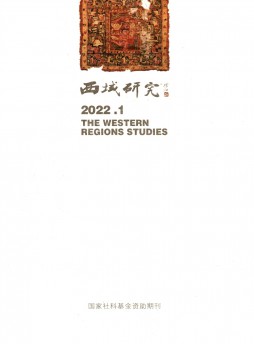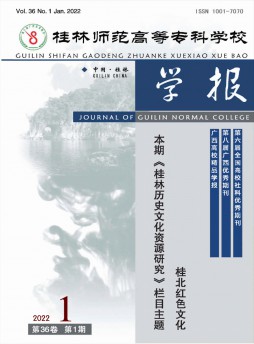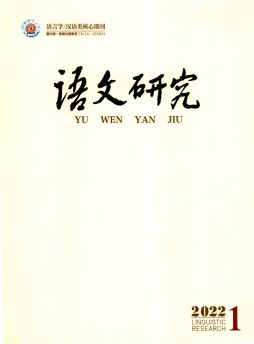西方美術(shù)論文范文
前言:我們精心挑選了數(shù)篇優(yōu)質(zhì)西方美術(shù)論文文章,供您閱讀參考。期待這些文章能為您帶來(lái)啟發(fā),助您在寫(xiě)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層樓。

第1篇
摘 要:本文通過(guò)對(duì)兒童藝術(shù)特點(diǎn)的剖析,揭示西方現(xiàn)代主義繪畫(huà)吸收和借鑒兒童藝術(shù)造型符號(hào)之后所形成的前所未有的率真、稚拙和清新的品質(zhì),并結(jié)合藝術(shù)家的具體作品分析進(jìn)一步指出西方現(xiàn)代主義繪畫(huà)在本質(zhì)上有別于兒童稚拙藝術(shù),張揚(yáng)著獨(dú)特的藝術(shù)個(gè)性,具有大巧若拙,拙中藏巧的藝術(shù)境界。
一、引 言
人們過(guò)去并未意識(shí)到兒童隨意而愉快的涂抹有什么特殊意義,更談不上對(duì)兒童藝術(shù)的發(fā)現(xiàn)及關(guān)注,然而,隨著人類(lèi)藝術(shù)史上對(duì)兒童藝術(shù)的發(fā)現(xiàn)及現(xiàn)代藝術(shù)的產(chǎn)生,兒童藝術(shù)在當(dāng)代藝術(shù)世界的位置正日益凸顯。現(xiàn)在,“兒童藝術(shù)”已是被普遍接受的概念,兒童藝術(shù)中那種形象的簡(jiǎn)化、畫(huà)面的和諧、富有表現(xiàn)力的線條、大膽的純色平涂以及那種無(wú)意識(shí)的創(chuàng)作狀態(tài),使得西方現(xiàn)代藝術(shù)家懷著新奇的目光從兒童藝術(shù)中汲取營(yíng)養(yǎng)。
二、西方現(xiàn)代主義藝術(shù)大師對(duì)兒童藝術(shù)的認(rèn)識(shí)與評(píng)價(jià)
兒童的作品究竟有何魅力?為什么會(huì)吸引全世界藝術(shù)家的目光?在兒童藝術(shù)中,兒童常常以其天真率直的心態(tài)每每使我們拍手稱快,是任何人為的方法都無(wú)法企及的。兒童藝術(shù)是無(wú)意識(shí)下創(chuàng)作的作品,是兒童心智和心緒的自然流露,往往呈現(xiàn)著藝術(shù)創(chuàng)作最初的也是最純粹的源泉。其構(gòu)圖造型稚拙有趣,似無(wú)法之法,有意想不到的生動(dòng)。正如黑格爾所說(shuō):“兒童是最美好的,一切個(gè)別特殊性在他們身上好像都還沉睡在未展開(kāi)的幼芽里,還沒(méi)有什么狹隘的東西在他們的胸中激動(dòng),在兒童還在變化的面貌上,還看不出承認(rèn)繁復(fù)意圖所造成的煩惱,因而在兒童繪畫(huà)里表現(xiàn)出來(lái)的是他們對(duì)事物無(wú)意識(shí)的、天真率直的看法。133229.cOm”兒童藝術(shù)更具創(chuàng)造性和表現(xiàn)性,注重個(gè)人感受。兒童天性充滿熱情,能主動(dòng)、自由地表現(xiàn)畫(huà)面,兒童看世界有他們自己的獨(dú)特眼光,他看起人來(lái),只看到一個(gè)人的一個(gè)大頭,頭上的兩只眼睛,一個(gè)鼻子,一張嘴巴,什么耳朵、頭發(fā)、眉毛,他都沒(méi)有看見(jiàn),所以他不畫(huà)一個(gè)人的身體,他看得不重要,只畫(huà)一條線來(lái)表示。這些入眼的觀察對(duì)象在兒童的心目中形象分外鮮明。兒童是畫(huà)其所想而非畫(huà)其所見(jiàn),因此兒童畫(huà)出的作品往往想象豐富,用色大膽,富有生氣,有更多的靈性。西方現(xiàn)代派藝術(shù)中,反叛傳統(tǒng),追求單純和質(zhì)樸無(wú)華是其共同的目的和重要特征,因此,現(xiàn)代藝術(shù)家們不約而同地將目光投向了兒童藝術(shù),而且給予兒童藝術(shù)以高度的評(píng)價(jià),甚至對(duì)兒童的藝術(shù)狀態(tài)和兒童的藝術(shù)作品崇拜不已。現(xiàn)代藝術(shù)大師畢加索曾說(shuō)過(guò):“我曾經(jīng)能像拉斐爾那樣作畫(huà),但我卻花了畢生的時(shí)間去學(xué)會(huì)像兒童那樣作畫(huà)。”這在當(dāng)時(shí)是很有代表性的。其實(shí)這種對(duì)兒童藝術(shù)的新的認(rèn)識(shí)和評(píng)價(jià)在野獸派那里已有所表現(xiàn)。康定斯基崇拜兒童藝術(shù)是因?yàn)樗J(rèn)為兒童藝術(shù)是對(duì)事物內(nèi)在本質(zhì)的直覺(jué)表現(xiàn),他說(shuō):“兒童除了描摹外觀的能力之外,還有力量使永久的內(nèi)在真理處在它最能有力地得以表現(xiàn)的形式中。……兒童有一種巨大的無(wú)意識(shí)力量,它在此表達(dá)自身,并且使兒童的作品達(dá)到與成人一樣高(甚至更高)的水平。”畫(huà)家馬蒂斯、杜飛、夏加爾,尤其是克利、米羅和杜布菲等,同樣感到了兒童藝術(shù)的魅力。西方藝術(shù)家所向往的那種無(wú)意識(shí)的創(chuàng)作狀態(tài)、“信手涂抹”在兒童藝術(shù)那里得到了很好的詮釋。
三、西方現(xiàn)代主義繪畫(huà)對(duì)兒童藝術(shù)的借鑒與模仿
從19世紀(jì)后半葉起,西方畫(huà)壇發(fā)生了重大變化,眼花繚亂的西方現(xiàn)代畫(huà)派,既受到兒童繪畫(huà)在藝術(shù)形式上以及表現(xiàn)技巧方面的啟發(fā),更受到兒童對(duì)待繪畫(huà)的基本態(tài)度無(wú)意識(shí)的強(qiáng)烈沖擊。對(duì)兒童藝術(shù)的推崇與模仿直接反映在他們作品的形式中。克利就一直崇拜兒童的這種天真狀態(tài),并以自己的方式加以模仿。克利在繪畫(huà)技巧上使用兒童那種環(huán)繞的、粗陋的輪廓線,反應(yīng)在作品《動(dòng)物園》、《他喊叫,我們玩》和《女舞蹈家》中,這些畫(huà)中線條技法與兒童素描的線條技巧很接近,盡管它更細(xì)窄,更優(yōu)美。《高架橋的革命》畫(huà)面上簡(jiǎn)單的甚至笨拙的高架橋,表現(xiàn)出了克利對(duì)兒童畫(huà)天真稚拙的形象以及符號(hào)化形象的興趣。在米羅的繪畫(huà)世界中同樣可以感受到這位大師對(duì)兒童藝術(shù)的推崇,在他1948年至1953年的許多繪畫(huà)作品中,人物沒(méi)有身體表現(xiàn),頭部直接安在以球形腳為末端的直腿上,整個(gè)臉像一個(gè)不規(guī)則的橢圓形或圓形,這種極端單純化的形象的變體,也就是兒童畫(huà)中的“蝌蚪人”樣式,如作品《在甲殼下部》、《黎明時(shí)瞪羚的哭叫》和《繪畫(huà)》以及早期最有名的作品《農(nóng)場(chǎng)》都已呈現(xiàn)出一種兒童般稚拙的風(fēng)格傾向。后來(lái)由于戰(zhàn)爭(zhēng),米羅的作品表現(xiàn)出前所未有的恐怖之感,但畫(huà)面依然保持他那種天真、優(yōu)美的風(fēng)格。如系列《星座》及《女詩(shī)人》都是在戰(zhàn)爭(zhēng)的威脅之下創(chuàng)作出來(lái)的,但我們從中看不到任何血腥的痕跡。無(wú)怪乎有批評(píng)家說(shuō):“米羅的天才是一種返老還童的天才。”涂鴉和兒童藝術(shù)也是杜布菲的范例和靈感來(lái)源,他特別贊同用最簡(jiǎn)單的正面和側(cè)面形象及兒童的輪廓線風(fēng)格畫(huà)出大腦袋粗陋人物,也贊同兒童對(duì)記憶中傳達(dá)信息的細(xì)節(jié)的強(qiáng)調(diào),杜布菲甚至希望以更加粗蠻、直接和確定的方式拋棄“后天學(xué)到的手段”,去探討一條回到“藝術(shù)基本的、形成的時(shí)期,記錄下兒童式的天真與好奇狀態(tài)的道路”。在他早期的作品中,如《街上的男人》畫(huà)面中描繪的是巴黎的景色與生活,具有一種天真稚拙的趣味。此后,他很快擺脫了克利藝術(shù)中那種幻想、略顯天真的氣質(zhì),而轉(zhuǎn)向一種獨(dú)特的、奠定自己在藝術(shù)史上地位的繪畫(huà)創(chuàng)作方法,創(chuàng)作出一些涂鴉形態(tài)的作品,如在《人間的聯(lián)歡節(jié)上》,我們可以看到的一種以此法創(chuàng)作出來(lái)的令人厭惡和不安的歡樂(lè)氛圍。
西方現(xiàn)代派藝術(shù)中的荒誕和隨意性與兒童藝術(shù)中的荒誕和隨意是一致的。“荒誕藝術(shù)比起優(yōu)美、崇高的藝術(shù)更加深刻地表現(xiàn)了人之所以為人的內(nèi)在生命力。”這是西方現(xiàn)代畫(huà)派對(duì)怪誕藝術(shù)的看法和推崇。現(xiàn)代派大師馬蒂斯、畢加索等人就從古代非洲的繪畫(huà)和雕塑中吸取怪異而又荒誕的特點(diǎn),在我們的眼中極不符合常規(guī),但這與兒童美術(shù)中的無(wú)意識(shí)荒誕的想法極為相似。西方現(xiàn)代主義繪畫(huà)對(duì)兒童藝術(shù)的接受主要表現(xiàn)在欣賞他們的天然和單純,使得他們的作品具有稚拙的面貌,法國(guó)評(píng)論家在觀看他們的畫(huà)展時(shí),曾稱這些顏色不符合“客觀實(shí)際”,藝術(shù)形象難以理解。雖說(shuō)在現(xiàn)在看來(lái)有點(diǎn)言過(guò)其實(shí),然而的確在馬蒂斯等人的作品中反映出畫(huà)家進(jìn)一步轉(zhuǎn)向表現(xiàn)內(nèi)心情感,這也是近現(xiàn)代以來(lái)西方繪畫(huà)逐漸擺脫傳統(tǒng)上摹寫(xiě)現(xiàn)實(shí)的主流畫(huà)法的新的一步,在野獸派繪畫(huà)中,馬蒂斯等畫(huà)家的一些人物畫(huà)有一個(gè)特點(diǎn),人物的形象往往有彎曲的形態(tài)和封閉的輪廓線。如馬蒂斯的《浴者》和《海濱婦女》,這些作品使人想起兒童藝術(shù)的某些特點(diǎn),人物的形象看起來(lái)“不準(zhǔn)確”。上述這些對(duì)兒童藝術(shù)語(yǔ)言的模仿甚至直接挪用只是一個(gè)方面,更重要的是現(xiàn)代藝術(shù)家們從兒童那里重新獲得天真、純樸和清新的內(nèi)在品質(zhì)。
四、現(xiàn)代主義繪畫(huà)大巧若拙
現(xiàn)代主義繪畫(huà)在許多方面更借鑒兒童藝術(shù),但他們的目的并非簡(jiǎn)單地重創(chuàng)兒童繪畫(huà),在技巧、表現(xiàn)形式上與兒童繪畫(huà)有很大差別。兒童繪畫(huà)是在生命之初對(duì)世界的探索嘗試,表達(dá)的是整個(gè)生命尚未展開(kāi)的天性。而大師的繪畫(huà)則是在生命成熟階段對(duì)探索世界的提煉總結(jié),表達(dá)出整個(gè)生命發(fā)展過(guò)程凝結(jié)出來(lái)的人格特征和藝術(shù)個(gè)性。所以,兒童畫(huà)一張張來(lái)看,大不相同,而大面積看起來(lái),其面貌給人的感覺(jué)大同小異。大師繪畫(huà)則不同,都具有獨(dú)一無(wú)二性。克利、米羅和杜布菲等現(xiàn)代畫(huà)家在對(duì)兒童藝術(shù)的借鑒中充分展示了各自的藝術(shù)個(gè)性,他們使用兒童的符號(hào)和技法也并非偶然,而是他們比其他藝術(shù)家更需要這種敏銳的感覺(jué)力,帶著激情去感受兒童的繪畫(huà)世界。他們的繪畫(huà)有著精致的層次和精湛的技巧,雖然繪畫(huà)的最終效果有著明顯的隨意性,但與兒童天真的藝術(shù)并未完全融合,保持著各自的獨(dú)立性,又相得益彰。兒童的繪畫(huà)作品是“原始”形態(tài)的、天真純樸的,而又往往以“稚拙”的樣式表現(xiàn)出來(lái)。這在兒童是很可貴的,也是許多中外畫(huà)家所追求的藝術(shù)境界。那么藝術(shù)家追求的天真純樸和稚拙與兒童繪畫(huà)所表現(xiàn)出的天真純樸和稚拙是否如出一轍呢?這對(duì)于我們更深一步了解兒童藝術(shù)是至關(guān)重要的。審美創(chuàng)造一般都是由拙到巧、再由巧返拙的階段。開(kāi)始之拙,是生疏幼稚的真拙,隨著審美創(chuàng)造技巧的提高,進(jìn)入精巧工巧階段,有了豐富的經(jīng)驗(yàn)、功夫、素養(yǎng),才能落盡繁華歸于樸淡,進(jìn)入大巧若拙的境界。沒(méi)有深厚的功底,片面為拙而拙,只會(huì)粗陋低俗。戴復(fù)古說(shuō):“樸拙唯宜怕近村。”(《論詩(shī)十絕》)即使是巧后之拙,如果刻意追求拙的外在形式,則是一種造作,失去其真正的天然本質(zhì)。拙樸絕非粗率平庸之輩所能達(dá)到的,它是審美創(chuàng)造高度成熟的標(biāo)志。追求兒童趣味的藝術(shù)家在某些方面與兒童繪畫(huà)較為相似,例如:以線為主,平涂色彩,不講焦點(diǎn)透視及夸張變形手法等等。但兒童藝術(shù)中的那種天真稚拙的情趣被藝術(shù)家們加以發(fā)揮、拓展,成為嶄新的藝術(shù)形式。雖然他們畫(huà)中的“拙”與兒童繪畫(huà)中的“拙”有著形式上的相似,但卻又有著本質(zhì)的區(qū)別:他們是老子所說(shuō)的“大巧若拙”之“拙”。寫(xiě)意大師崔子范也曾說(shuō):“一個(gè)沒(méi)有受過(guò)專業(yè)訓(xùn)練的孩子只憑熱情作畫(huà)。在他長(zhǎng)大之后,也應(yīng)該注意使自己回到童年的心態(tài),去重新發(fā)掘自己兒時(shí)的天性——自由地而不是造作地在畫(huà)中表現(xiàn)自己的感情。當(dāng)一個(gè)成熟的畫(huà)家運(yùn)用這種方式作畫(huà)時(shí),當(dāng)他將藝術(shù)大師的精湛技巧與孩子般的天真爛漫融合在一起時(shí),會(huì)感到極大的快慰。”雖然西方的克利、米羅和杜布菲等畫(huà)家的作品源于兒童繪畫(huà)的造型符號(hào),但他們靠熟練精深的技巧來(lái)完成。大體上都經(jīng)歷了由開(kāi)始的不成熟,到技法日趨精深,進(jìn)而追求“返璞歸真”的過(guò)程。雖然也有追求兒童“拙味”的畫(huà)家未經(jīng)過(guò)專門(mén)的訓(xùn)練,但他們也難免經(jīng)受藝術(shù)傳統(tǒng)的熏陶,前輩及同代畫(huà)家的影響與個(gè)人技巧的錘煉。克利雖曾說(shuō):“無(wú)需什么技巧”,但他畢竟經(jīng)過(guò)了傳統(tǒng)藝術(shù)熏陶,其藝術(shù)風(fēng)格必有傳統(tǒng)技巧的痕跡。可見(jiàn)兒童的稚拙是幼稚的拙,而畫(huà)家的稚拙是“拙中藏巧”之拙。“拙樸最難,拙近天真,樸近自然,能拙樸則渾厚不流為滯膩。”拙樸之拙,是大巧,不露痕跡,使人不覺(jué)其巧。它是“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實(shí)濃”(《東坡題跋》),在平實(shí)樸素粗散的形式中,蘊(yùn)含著深厚的審美素養(yǎng)和豐富的情感意味。沒(méi)有一定技巧的錘煉,一味片面追求兒童“拙味”,只會(huì)流于粗俗淺薄,達(dá)不到自然渾化的拙樸之境。
五、結(jié) 語(yǔ)
總之,現(xiàn)代藝術(shù)家們從兒童藝術(shù)中獲取到了造型符號(hào)的靈感,同時(shí)也通過(guò)自己的作品和言論促成了人們對(duì)兒童藝術(shù)的進(jìn)一步關(guān)注、承認(rèn)和了解。在現(xiàn)代藝術(shù)中,傳統(tǒng)的審美標(biāo)準(zhǔn)首先被打破,幾乎沒(méi)有什么尺度可以將兒童藝術(shù)與大師的作品相區(qū)別。當(dāng)然,西方現(xiàn)代主義藝術(shù)家的作品與兒童的繪畫(huà)作品之間的相仿程度,也不能真正完全劃上等號(hào),這些現(xiàn)代藝術(shù)大師的繪畫(huà)畢竟是落盡繁華歸于樸淡,大巧若拙,拙中藏巧。
參考文獻(xiàn):
[1] 羅伯特·戈德沃特.現(xiàn)代藝術(shù)中的原始主義[m].殷泓譯.南京:江蘇美術(shù)出版社1993:54.
[2] 阿恩海姆.藝術(shù)與視知覺(jué)[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3] 崔慶忠.現(xiàn)代美術(shù)史話[m].北京:人民美術(shù)出版社2001.
第2篇
關(guān) 鍵 詞:現(xiàn)代繪畫(huà) 交流 融合 影響
西方近代美術(shù)史的演變,曾被人喻為一個(gè)傳奇性的故事。由19世紀(jì)末到20世紀(jì)初,人們千變?nèi)f化的價(jià)值觀念,打開(kāi)了許多未曾探索過(guò)的道路。一直到現(xiàn)在,“現(xiàn)代美術(shù)”仍是個(gè)令人迷惑的名詞,一些被公認(rèn)為藝壇巨人的畫(huà)家,如塞尚、馬蒂斯、畢加索雖已成為藝術(shù)史上的傳奇人物,卻仍然經(jīng)常被一般人所忽略,畢加索的立體派或荒唐或有趣,馬蒂斯的野獸主義或美觀或滑稽。但是這些“巨人”是如何創(chuàng)造出如此與眾不同的藝術(shù)流派的呢?他們的經(jīng)歷既辛酸又坎坷。在現(xiàn)代歐洲藝壇中,野獸派代表人物馬蒂斯,西班牙超現(xiàn)實(shí)主義畫(huà)家、抽象派繪畫(huà)的先驅(qū)者米羅,兼具立體主義、超現(xiàn)實(shí)主義、表現(xiàn)主義等多種風(fēng)格的俄國(guó)斯畫(huà)家夏卡爾,均為極負(fù)盛名的大師,被推崇為藝壇一代宗師。
1910年,馬蒂斯在慕尼黑觀賞了轟動(dòng)一時(shí)的近東藝展,那次藝展對(duì)于他日后的繪畫(huà)方式,有著不可磨滅的影響力。近東的藝術(shù)富于艷麗逼人的色彩,而且也偏重于平面式的構(gòu)圖,用強(qiáng)烈而鄉(xiāng)間的純色彩、阿拉伯式的藤蔓花紋和各種只有東方味道的平面圖案。在他繪畫(huà)生涯的后期,馬蒂斯開(kāi)始用彩色的紙,剪成彩色圖案,再用蠟筆和塑膠水彩來(lái)掩飾晚年以及疾病帶給他的不便。WWw.133229.CoM馬蒂斯的藝術(shù)之所以不朽,因?yàn)樗萘舜笞匀唬軌蜃屪约和笞匀缓隙橐唬c大自然的韻律起步而行。這一點(diǎn)同我國(guó)老子、莊子的順其自然頗為近似。“莊周夢(mèng)蝴蝶,蝴蝶夢(mèng)莊周,萬(wàn)體更變易,萬(wàn)事良悠悠。”“萬(wàn)體更變易”便是馬蒂斯所強(qiáng)調(diào)的重點(diǎn)之一,人在不同的時(shí)候看同樣的一件東西,觀察的角度不可能完全一樣。西方美術(shù)自14、15世紀(jì)文藝復(fù)興以來(lái),一向強(qiáng)調(diào)“獨(dú)一立足點(diǎn)”論,這是與東方美術(shù)完全不同的地方。東方美術(shù)幾乎不使用一個(gè)固定的立足點(diǎn),一幅畫(huà)總是由許多不同的立足點(diǎn)來(lái)構(gòu)成,馬蒂斯所擁有的,就是我們東方美術(shù)的這種“多重立足點(diǎn)”的觀念。因此他的畫(huà)顯得格外生動(dòng)活潑,一點(diǎn)也不死板。馬蒂斯的空間利用恰巧符合我們“陰陽(yáng)相間”的理論。馬蒂斯利用空間促使了畫(huà)中物體間氣韻的順暢,舉世聞名的現(xiàn)代美術(shù)評(píng)論家羅杰·弗萊在1912年評(píng)論馬蒂斯是所有西洋畫(huà)家中最了解中國(guó)美術(shù)精神的一位,這種啟發(fā)生命的韻律感,以及相對(duì)論的道理,確實(shí)是中國(guó)美術(shù)所強(qiáng)調(diào)的重點(diǎn)。他還認(rèn)為:“第十、十一、十二世紀(jì)的藝術(shù),亦即羅馬式藝術(shù),包含很多東方藝術(shù)的成分,這些成分在當(dāng)時(shí)還伴隨其他貨品,由東方輸入伊斯坦布爾、威尼斯,這些成分貢獻(xiàn)很多,它們經(jīng)過(guò)轉(zhuǎn)變,有了新的生命,而顯豐饒,它們開(kāi)發(fā)新道路,也形成新環(huán)節(jié)。1920年的《宮女》,畫(huà)中的東方色彩(尤其是對(duì)波斯纖細(xì)畫(huà)的喜愛(ài))以及作者筆下簡(jiǎn)單的僧侶式人體、繁縟的背景同樣是扣人心弦的組合。他對(duì)線條的抽象、和諧、節(jié)奏的追求,強(qiáng)烈得常使人體的自然表象剝落盡至。”這樣的說(shuō)法是正確的,無(wú)論如何,這時(shí)期的畫(huà)意念非常豐富,人體的簡(jiǎn)化與靜物畫(huà)裝飾細(xì)節(jié)的增濃并進(jìn)。原因之一,是他長(zhǎng)久以來(lái)對(duì)東方藝術(shù)的喜愛(ài),這份喜愛(ài)在1910年9月他赴慕尼黑參觀回教藝術(shù)展時(shí)達(dá)到巔峰,后來(lái)他曾說(shuō):“我的靈感是來(lái)自東方。波斯纖細(xì)畫(huà)啟示我感官的一切可能,緊密的細(xì)節(jié)暗示出更大的空間,并幫我超越披露個(gè)人感情的繪畫(huà)表現(xiàn)。”馬蒂斯非常喜歡阿拉伯的蔓藤花,是緣于回教藝術(shù)的直接影響(日本版畫(huà)也有)。“我曾用彩色的紙做了一對(duì)小鸚鵡,我在作品中找到自己,中國(guó)人說(shuō)要與樹(shù)齊長(zhǎng),我認(rèn)為再也沒(méi)有比這句話更認(rèn)真的了。”馬蒂斯晚年熱衷于剪紙藝術(shù)時(shí)說(shuō)了這段獨(dú)白,他把東方的剪紙視為完全美的化身,從剪紙畫(huà)中得到過(guò)去從未有過(guò)的平衡境界。不取西方古典油畫(huà)的三維立體塑造,基本上是在二維空間的平面構(gòu)成中展示自己的彩色夢(mèng)幻。但是由于彩色板塊里加進(jìn)了黑白板塊的分割、隔離以及物象的排映、濃濃的交織,畫(huà)面呈現(xiàn)出多重的空間層次,不僅生成平面的張力,而且生成縱深的張力,從而產(chǎn)生一種疊幻的視覺(jué)牽引力,使畫(huà)面欣賞起來(lái)如層層剝筍,十分耐品。他的靈感常常來(lái)自東方藝術(shù),用純色平涂,色彩鮮艷,但并不“野獸”般刺激,他夢(mèng)想的是一種平衡、純潔、寧?kù)o,不含有使人不安或令人沮喪的題材的藝術(shù),它像一種鎮(zhèn)定劑,或者像一把舒適的安樂(lè)椅。
在西方現(xiàn)代畫(huà)家中,保羅克利對(duì)東方人來(lái)說(shuō)是最親近的。他的藝術(shù)觀念和東方神秘主義相通,即把創(chuàng)作活動(dòng)視為不可思議的體驗(yàn),而這一體驗(yàn)過(guò)程乃是內(nèi)部幻覺(jué)與外界真實(shí)的統(tǒng)一,其哲學(xué)根源在人和自然之間本質(zhì)上的同一性。
自1916年至1917年,克利專攻中國(guó)文學(xué),接觸到中國(guó)書(shū)法和中國(guó)畫(huà),從中汲取了文字可以造型的思想,并以獨(dú)特的方式進(jìn)行了實(shí)驗(yàn)。這一研究結(jié)果就是一系列的文字畫(huà)。而且以后還以單個(gè)的較大r字母出現(xiàn)在繪畫(huà)中,克利的繪畫(huà)藝術(shù)中,體現(xiàn)了中國(guó)繪畫(huà)的影響,在《隱士的住所》中的那所簡(jiǎn)陋的小屋,是中國(guó)山水畫(huà)的面貌,不過(guò),在這幅作品中,房屋的側(cè)面卻豎有十字架,它告訴人們這位隱士不是中國(guó)人。克利在藝術(shù)上與中國(guó)最重要的關(guān)系,與其說(shuō)是主題還不如說(shuō)主要表現(xiàn)在繪畫(huà)內(nèi)容上,尤其在中國(guó)文學(xué)中常見(jiàn)的大自然與孤獨(dú)者之間的對(duì)話,對(duì)克利產(chǎn)生了強(qiáng)烈的共鳴;與其說(shuō)是受到中國(guó)的影響,還不如說(shuō)是對(duì)中國(guó)的再認(rèn)識(shí)。如他畫(huà)的《中國(guó)風(fēng)俗畫(huà)i》《中國(guó)風(fēng)俗畫(huà)工ii》和《曾經(jīng)在灰蒙蒙的夜色下徘徊》一樣,本來(lái)是完整的一幅,后來(lái)被裁為各不相同的兩幅作品,旨在表現(xiàn)中國(guó)油畫(huà)的風(fēng)格。他在創(chuàng)作《中國(guó)風(fēng)俗畫(huà)》前還有一個(gè)作品,編號(hào)是《中國(guó)陶器》。由此看來(lái),在一段時(shí)間內(nèi),克利對(duì)中國(guó)產(chǎn)生了很深的感情。《大路與小徑》,都融會(huì)在這大大小小完全抽象的格狀作品中,垂直線和畫(huà)面,象征著廣闊的埃及原野,它們以多變的寬度,向著頂端的天藍(lán)色帶——尼羅河延伸;在斑斕的色彩映照下,廣闊的田野與顫動(dòng)的空氣融為一體,大地流水、太陽(yáng)、春光充滿著永恒的詩(shī)一般的境界,整個(gè)畫(huà)面形式與韻律結(jié)構(gòu)氣勢(shì)恢宏,這(轉(zhuǎn)第105頁(yè))(接第108頁(yè))與中國(guó)講究的人與自然相融合至高境界的理念是相符的。
克利在晚年的繪畫(huà)中使用很粗的線條,有些像中國(guó)的書(shū)法,“筆跡最關(guān)鍵的是表現(xiàn)而不是工整,請(qǐng)考慮一下中國(guó)人的做法。我們?cè)诜磸?fù)練習(xí)的過(guò)程中,才能使筆跡變得更為細(xì)膩、更直觀、更神韻。”這是他的體會(huì),克利依靠自己高度集中的精神,達(dá)到了與東方藝術(shù)家并駕齊驅(qū)的境界。像《鼓手》這幅畫(huà),乍看幾乎和中國(guó)現(xiàn)代書(shū)法差不多:像“寫(xiě)字”一樣的單純的黑色線條,在簡(jiǎn)潔的形態(tài)中隱藏著深切的感動(dòng)。此時(shí),克利的手足已不能自由活動(dòng),于是他用最少的視覺(jué)語(yǔ)言記下了最后最多最明確的話語(yǔ),熱愛(ài)音樂(lè)的克利,回憶起少年時(shí)代作為一名鼓手參加伯爾尼市管弦樂(lè)團(tuán)的演奏,便創(chuàng)作了這幅畫(huà)。大大的眼睛,強(qiáng)有力的胳膊,以及畫(huà)面的深紅色,表示他自己對(duì)人生執(zhí)著的追求,同時(shí)讓人感到在內(nèi)部隱藏著冷酷的命運(yùn)。常常“先行而后思”,不斷在實(shí)踐中思考總結(jié)自己的創(chuàng)作經(jīng)驗(yàn)。參照他的繪畫(huà),可以看出他“緊緊抓住‘綜合鏈條’,通過(guò)‘博大精深’,走向‘天人神會(huì)’”的創(chuàng)作思路。“天人神會(huì)”是克利追求的最高境界。畫(huà)天宇、畫(huà)日月,亦可見(jiàn)其所求。“博大精深”是克利經(jīng)歷的意象升華。他認(rèn)為繪畫(huà)語(yǔ)言的“非陳述性”表現(xiàn)為直觀性、可感性、符號(hào)性、有機(jī)性、意象性;而這些特性在中國(guó)畫(huà)里則體現(xiàn)為既非“具象”也非“抽象”而是“主客觀高度濃縮統(tǒng)一的形象”,即超乎“具象”與“抽象”的“意象”和“意境”。
筆者聯(lián)想到與之視覺(jué)語(yǔ)匯相近的中西兩種藝術(shù):一是漢代畫(huà)像石的拓片。漢代畫(huà)像磚、畫(huà)像石的拓片就是一種影像,是不見(jiàn)骨線卻很有力度、很有動(dòng)感的一種影像。東方思維方式不像西方那樣主客對(duì)立、內(nèi)外分明,但由于修養(yǎng)、閱歷和個(gè)性之異亦各有所側(cè)重。
第3篇
《圣經(jīng)·馬太福音》曾說(shuō):“在黑暗中開(kāi)黎明”。這一語(yǔ)道破了光在這個(gè)世界中的位置,因?yàn)樗且磺腥f(wàn)物得以顯現(xiàn),并且被賦予生命的神奇物質(zhì)。同樣,在研究或欣賞西方繪畫(huà),尤其是傳統(tǒng)繪畫(huà)時(shí),我們更不能忽視光的神奇力量。光在西方繪畫(huà)中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
有了光,便有了體積,有了形狀,有了色彩。因此,西方繪畫(huà)對(duì)光的運(yùn)用集中體現(xiàn)在真實(shí)性藝術(shù)之中,要粗略給個(gè)范圍的話。這大概是從古希臘開(kāi)始,一直延續(xù)印象主義,這以后的藝術(shù)雖然仍有不少具象繪畫(huà),但就整個(gè)藝術(shù)史來(lái)看,它已經(jīng)不再是主流,所以從現(xiàn)代主義開(kāi)始的西方繪畫(huà)不在本文討論的范圍之內(nèi)。
在西方繪畫(huà)史的長(zhǎng)河中,對(duì)光的運(yùn)用大致可分為三個(gè)階段。第一階段從古希臘羅馬到文藝復(fù)興。在這個(gè)時(shí)期,對(duì)光的運(yùn)用是為了通過(guò)制造幻覺(jué)達(dá)到描述的作用。藝術(shù)從古埃及到古希臘的轉(zhuǎn)變。正是古希臘人認(rèn)識(shí)到光的重要,從而認(rèn)識(shí)到明暗。認(rèn)識(shí)到色彩,達(dá)到對(duì)真實(shí)的表現(xiàn)。古羅馬的繪畫(huà)在龐貝和赫庫(kù)蘭·尼姆的死者肖像中可略知一二,在這些繪畫(huà)中,我們看不到太多的“光”,它們是通過(guò)把光消解在陰影和明暗中來(lái)摹擬物象,是對(duì)光被動(dòng)地接受,光化為了形體。在中世紀(jì),古希臘、羅馬的繪畫(huà)傳統(tǒng)在拜占庭帝國(guó)中得到延續(xù),以至以后的印象派畫(huà)家雷諾阿在威尼斯圣·馬可大教堂看到拜占庭的畫(huà)時(shí)發(fā)出感嘆,認(rèn)為光和色的奧秘早已被中世紀(jì)的畫(huà)家所識(shí)破。WWw.133229.CoM
第二階段從文藝復(fù)興到十八世紀(jì),在這個(gè)階段對(duì)光的運(yùn)用可用一個(gè)詞來(lái)概括:設(shè)計(jì)。對(duì)光的運(yùn)用強(qiáng)調(diào)一種人工性的設(shè)計(jì),這基于對(duì)光的獨(dú)立表現(xiàn)力的認(rèn)識(shí),光并不只是為了造成塑造形體的明暗。而且是為了氣氛、環(huán)境的渲染或體現(xiàn)畫(huà)家的某種思想。馬薩喬是自喬托之后第一個(gè)在才能上與之不相上下的畫(huà)家,從他的處女作《寶座上的圣母子和二天使》中可以看出,他的革新精神已初露鋒芒,他的人物較之喬托的畫(huà)更加真實(shí)有力,畫(huà)中的背景具有一種親切的真實(shí)感。同時(shí)還證明他是通過(guò)光第一個(gè)廣泛運(yùn)用明暗對(duì)比手法的人;第一個(gè)掌握透視法的人。馬薩喬的業(yè)績(jī)給同時(shí)代的和后來(lái)的畫(huà)家們以極大的影響,他們?yōu)榱藢W(xué)習(xí)馬薩喬的技法,研究他完美的寫(xiě)實(shí)技巧、空間的表現(xiàn)、人物的安排和優(yōu)美的造型,并最終形成了佛羅倫薩畫(huà)派的寫(xiě)實(shí)主義潮流。文藝復(fù)興的盛期美術(shù)一方面總結(jié)了十五世紀(jì)美術(shù)的經(jīng)驗(yàn)。把透視、解剖、明暗等寫(xiě)實(shí)的手法發(fā)展到了盡善盡美的地步:另一方面有汲取了古典藝術(shù)的優(yōu)秀傳統(tǒng),形成了莊重典雅的藝術(shù)面貌。同時(shí),大師們進(jìn)一步把藝術(shù)與實(shí)驗(yàn)科學(xué)、創(chuàng)作實(shí)踐與理論研究結(jié)合起來(lái),進(jìn)一步推進(jìn)了寫(xiě)實(shí)主義的創(chuàng)作。
在這一階段對(duì)光的設(shè)計(jì)歸納起來(lái)有兩種:一種是燭光效果,以尼德蘭的托特·辛特·楊斯的《基督誕生》及法國(guó)的喬治·拉圖爾的“夜間畫(huà)”為代表:另一種影響最大的是明暗對(duì)比效果,從達(dá)·芬奇的“漸隱法”開(kāi)始(作品《蒙娜麗莎》便可看出其成就)。到卡拉瓦喬的“酒窖光線法”(預(yù)示著歐洲十七世紀(jì)現(xiàn)實(shí)主義繪畫(huà)發(fā)展到了一個(gè)新的階段),再到倫勃郎的“明暗法”。在這個(gè)設(shè)計(jì)光線的階段,著重的是一種亮與暗的對(duì)比,在這種對(duì)比中既表現(xiàn)出形象,也傳達(dá)出一種形而上的思想。可見(jiàn)這時(shí)光的運(yùn)用已成為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