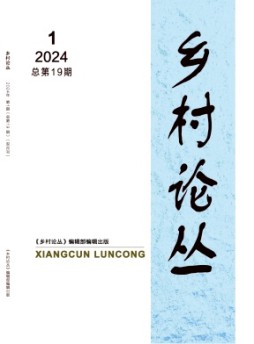鄉(xiāng)村精英社會流動的內在機制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鄉(xiāng)村精英社會流動的內在機制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雜志》2014年第三期
一、政治機制:鄉(xiāng)村控制的松動與鄉(xiāng)村治理的精英容納力不足
鄉(xiāng)村精英群體的重構與流動并不存在明顯的時間上的先后,重構與流動的過程是混合在一起的。改革開放引發(fā)了中國整個鄉(xiāng)村社會結構的變化,其典型的變化是在鄉(xiāng)村生產經營模式的變革———家庭聯(lián)產承包責任制之后,國家政治權力從鄉(xiāng)村逐漸回收,鄉(xiāng)村被賦予更多的自主權。在國家對鄉(xiāng)村社會控制松動的背景下,出現(xiàn)了一個相對自由的“行動空間”。對這一過程,鄭杭生教授有過經典的描述:“當前中國正處在兩個轉變之中:一是從農業(yè)的、鄉(xiāng)村的、封閉半封閉的傳統(tǒng)型社會,向工業(yè)的、城鎮(zhèn)的、開放的現(xiàn)代社會的轉變,這是社會結構的轉型;二是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這是經濟體制的轉軌。”⑥具體而言,這種宏觀社會結構的變化,最終轉化為鄉(xiāng)村精英社會流動的機制,這一機制由政治控制的松動、鄉(xiāng)村政治的轉型與政治利益訴求變化三個層面所構成。首先,鄉(xiāng)村政治管理體制變革,為鄉(xiāng)村精英的社會流動提供了制度上的可能性。在這一時期,國家對農村行政權力和組織的控制逐漸弱化,把其原有的控制權逐漸轉讓給鄉(xiāng)村自身,同時逐漸搭建起充分發(fā)揮農民能力的公平競爭平臺。這種鄉(xiāng)村自主性的獲得,使得鄉(xiāng)村精英群體有了自我行動的政治基礎,有了憑借自我能力去更廣闊市場領域競爭的制度保障,為其流動提供了合法依據(jù)。另外,國家對農民身份控制的逐漸弱化———以戶籍限制為中心的改革,⑦也成為鄉(xiāng)村精英流動的巨大推動力。20世紀80年代以來戶籍制度的松動,即城市對農村戶籍的有限容納,為鄉(xiāng)村優(yōu)勢人才進入城市并在城市尋找自己的發(fā)展空間破除了基本障礙。改革開放后形成了大規(guī)模的“民工潮”———其中的主力軍是鄉(xiāng)村的優(yōu)勢勞動力,當然包括鄉(xiāng)村精英群體,而非多年來學術界一直指稱的“剩余勞動力流動”。這一大規(guī)模的農民流動對嚴格的戶籍制度造成再度沖擊,中央和地方不得不對戶籍制度作出一系列的調整,由限制逐漸變得寬松,很多地方實行“綠卡戶籍制”,一些改革開放的前沿城市還普遍實行了“藍印戶口”,以吸引人才和資金。⑧由于戶籍制度的松動,原來嚴格的地域限制也逐漸弱化,鄉(xiāng)村精英可以自主決定自我發(fā)展的地域、領域與產業(yè)。科瑟指出:“如若統(tǒng)治者精英或非統(tǒng)治者精英試圖拒絕來自公眾的更新更具才華的成分輸入,如果精英的流通被阻塞,那么,就會破壞社會均衡,就會使社會秩序紊亂。”
⑨這一問題也正是中國改革開放進展中所著力解決的,鄉(xiāng)村精英群體便是在這一大的政治背景之下開始了在城鄉(xiāng)之間的流動。其次,城市與鄉(xiāng)村的二元政治結構也是推動鄉(xiāng)村精英流動的重要政治力量。城市的政治優(yōu)勢及其公共產品提供機制與水平,是改革開放之后的鄉(xiāng)村仍然無法與之相比的。在城市的政治體系中,以公共基礎設施建設為基礎,以公共服務為目的的政府政策安排與政府行為異常明顯。無論是有關城市的公共政策、城市管理制度以及城市服務的公共財政支出,還是城市管理與服務的人員配備,都遠遠優(yōu)于農村。有很多政府職能在城市是重要職能,比如垃圾處理、城市管理執(zhí)法、社區(qū)服務等,在鄉(xiāng)村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弱化和虛化。從城市與農村公民的政治參與途徑、意識、手段等層面,城鄉(xiāng)也明顯表現(xiàn)出一種二元性特征。徐勇教授認為,中國文明史一直是伴隨著城市與鄉(xiāng)村分離、對立過程進行的,而且具有鮮明的獨特性,政治社會狀況的城鄉(xiāng)差別和不平衡尤為突出。這種不平衡性正是一個國家政治發(fā)展的重要特點,并制約著整個社會的發(fā)展進程。⑩應當明確,城鄉(xiāng)經濟發(fā)展的二元化所依托的是農業(yè)與工業(yè)二者的差異,而政治二元化特征的存在,無疑使城鄉(xiāng)同一的公共權力運行呈現(xiàn)出二元化,成為諸多農村問題的癥結所在,“只有深入到作為中國政治舞臺基礎的城市和鄉(xiāng)村政治內部機器相互間的二元結構,才能科學地解釋發(fā)生在中國政治舞臺上撲朔迷離的景觀”。同樣,這種城鄉(xiāng)政治的二元化,使得鄉(xiāng)村精英群體整體上趨向于具有絕對政治優(yōu)勢的城市,這符合精英群體本身能力卓越的本質。第三,鄉(xiāng)村自治制度的不完善與精英吸納力不足,從客觀上造成了鄉(xiāng)村精英的流失。村民自治是我國推進基層民主制度的重要舉措,在村民自治制度中,選舉是最基礎、最重要的一環(huán)。但從村民自治制度來分析,關于選舉的相關制度并不完善,同時存在著制度與現(xiàn)實脫節(jié)的現(xiàn)象,其中最突出的問題是由法律制度不健全導致的賄選現(xiàn)象嚴重,發(fā)達地區(qū)、中等發(fā)達地區(qū)、不發(fā)達地區(qū)各占25.8%、36.9%、37.3%,瑏瑢村民選舉成為權錢交易的舞臺。與賄選并存的是上級指派村干部取代村民直選,鄉(xiāng)鎮(zhèn)政權向鄉(xiāng)村延伸,控制村委會換屆選舉。這些問題嚴重影響了鄉(xiāng)村精英的參政熱情,在很多地區(qū)甚至出現(xiàn)政治冷漠。并且,在村民選舉過程與結果的具體落實等層面,也缺乏有效的可操作性規(guī)定,有些規(guī)定僅僅是原則性的。此外,村委會是村民自治組織,從其設置的目的來看是為了管理農村公共事務,但是我國大多數(shù)村委會的職能傾向于鄉(xiāng)鎮(zhèn)政府職能在村的延伸,村委會在不同程度上成了鄉(xiāng)鎮(zhèn)政府在村的執(zhí)行機構,村委會成了鄉(xiāng)鎮(zhèn)政府的代言人,而非代表村民,村委會的角色出現(xiàn)了錯位。
這種角色錯位使農民失去了參政熱情,積極性降低。尤其是在現(xiàn)有的村民自治框架中,鄉(xiāng)村精英的政治參與與政治利益訴求得不到滿足,政治參與熱情和鄉(xiāng)村政治現(xiàn)實的落差,使鄉(xiāng)村精英們產生了挫折感和挫敗感。一方面,國家在全國范圍內的鄉(xiāng)村自治與基層民主政治建設,使得鄉(xiāng)村精英群體在開始階段的政治參與期望值不斷高漲,當然,這種熱情也經歷了由感性到理性的一個轉變過程。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80年代以前,農民對政治社會的認同,主要建立在新社會使農民翻身解放的直觀體驗和對解放自己的領袖的深愛和無限敬仰的感情上。80年代以來,農民開始運用理性認識選擇其政治態(tài)度。”另一方面,我國鄉(xiāng)村基層民主政治建設中存在的選舉落實不力、鄉(xiāng)鎮(zhèn)政權干涉干部選任等問題,使鄉(xiāng)村精英的現(xiàn)實需求得不到滿足,產生了政治參與的挫折感,加之每次選舉出來的村委會成員也并未給村民帶來多少可以量化的實際利益,因而普通村民對村委會選舉自然就有了一種不自覺的心理抵觸,這些村民對村莊內的政治事務越來越冷漠。瑏瑥在鄉(xiāng)村自治制度不完善與鄉(xiāng)村治理的精英容納力低下的雙重因素影響下,鄉(xiāng)村精英的政權參與機會與政治參與效果與普通村民無異,因此,他們必然憑借其掌握的知識、技術等優(yōu)勢離開鄉(xiāng)村,涌入城市,以追求自身利益的實現(xiàn)和價值的滿足。在這一過程中,鄉(xiāng)村精英對于政治利益的追求仍可以實現(xiàn),他們可以在鄉(xiāng)村選舉或其他鄉(xiāng)村治理事務的討論中返鄉(xiāng)參與。由此可見,鄉(xiāng)村精英的外流并未削弱其基本的有限政治影響,這與離開鄉(xiāng)村涌入城市尋找自我利益并不矛盾。因此,現(xiàn)有的鄉(xiāng)村政治體系為鄉(xiāng)村精英的社會流動提供了可能性和現(xiàn)實性。
二、經濟機制:利益導向與城鄉(xiāng)經濟二元結構的影響
在鄉(xiāng)村精英流失的諸種機制中,經濟利益的導向是最為核心的力量。改革開放過程中鄉(xiāng)村最大的變化是農業(yè)生產與經營方式的變化,市場經濟的推動與農村改變自身落后的迫切意愿相呼應,使得經濟力量成為影響當前中國農村發(fā)展的最重要力量。當然,經濟力量對鄉(xiāng)村社會的重塑并非是單一維度的,社會結構、價值觀念與農民群體本身,都受到了市場經濟力量的沖擊,鄉(xiāng)村精英的社會流動正是鄉(xiāng)村精英對市場力量的回應與反應。具體而言,市場經濟發(fā)展所塑造的城市與鄉(xiāng)村之間不同程度的發(fā)展是鄉(xiāng)村精英社會流動的整體經濟框架;現(xiàn)代農業(yè)產業(yè)的勞動力容納力與農業(yè)現(xiàn)實收益低是鄉(xiāng)村精英社會流動的現(xiàn)實動力;農業(yè)機械化與土地流轉的集約化是鄉(xiāng)村精英社會流動的推動力量。改革開放后,作為理性經濟人的精英們自然會去努力尋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這是改革開放后的諸種經濟因素能夠推動精英群體社會流動的最基本的動力,這種動力多年來曾經被鄉(xiāng)村公社與集體經濟體系所禁錮與壓制,在此時得到了極大程度的宣泄和釋放。精英群體向能夠使自己經濟利益最大化的領域、區(qū)域與行業(yè)轉移,就成為鄉(xiāng)村發(fā)展過程中的一種必然。而改革開放后,中國經濟的高速發(fā)展所伴隨的是經濟發(fā)展的不均衡,城鄉(xiāng)二元結構體制下經濟發(fā)展呈現(xiàn)出巨大的經濟發(fā)展水平差異。當然,城鄉(xiāng)二元體制所導致的城鄉(xiāng)差別并非改革開放之后才出現(xiàn)的。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物質勞動和精神勞動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鄉(xiāng)村的分離。城鄉(xiāng)之間的對立是隨著野蠻向文明的過渡、部落制度向國家過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過渡而開始的,它貫穿著全部文明的歷史并一直延續(xù)到現(xiàn)在。”
但是,改革開放后的城鄉(xiāng)二元結構呈現(xiàn)出新的發(fā)展特征,突出地表現(xiàn)為宏觀上框定城鄉(xiāng)二元結構的政治體制已經逐漸得以消除,城鄉(xiāng)各自發(fā)展的獨立、平等的主體地位得到了確認,二者也因此獲得了應然層面自我發(fā)展的空間。但在現(xiàn)實中,城鄉(xiāng)兩個區(qū)域以及兩個區(qū)域中所容納的產業(yè)發(fā)展卻產生了多元化、多維度的經濟、政治與社會發(fā)展程度的差距———這比原來政治城鄉(xiāng)二元結構之下的差距還要大。城鄉(xiāng)經濟發(fā)展不平衡使得農村土地附加值過低,無論依托于土地的農業(yè)生產方式如何變革,在現(xiàn)有的生產環(huán)境與要求約束之下,土地能夠帶給農民的收益空間是有限的,這種收益增長的有限性與鄉(xiāng)村精英群體能力之間不能形成有效的互動。一般來說,土地附加值是一種對土地原有價值的超越,這種超越憑借生產方式變革、新技術的實現(xiàn)與勞動效率的提高得以實現(xiàn),當農村基本的生產活力被激發(fā)之后,土地附加值增加的實現(xiàn)區(qū)間基本是固定化的。這種農業(yè)土地附加值過低的現(xiàn)實是產業(yè)發(fā)展缺乏基本動力的根源所在。其中,對于農民群體最直接的影響在于同樣的勞動付出,在不同產業(yè)之間會獲得不同的收益,農民群體對農業(yè)的擺脫就成了一種必然選擇。在這種必然選擇過程中,城市中第二、三產業(yè)的大量勞動力需要首先吸引了具有競爭能力的優(yōu)勢勞動力群體———這其中包括鄉(xiāng)村精英群體。有數(shù)據(jù)顯示,雖然人民生活水平有了較大提高,但是城鄉(xiāng)居民收入差距卻在持續(xù)擴大。“城鎮(zhèn)居民收入大約是農村居民收入的1.8—3.4倍。城鄉(xiāng)居民收入差距自1985年達到歷史最低點1.86∶1后呈逐漸擴大趨勢,城鎮(zhèn)居民收入增長幅度高于農村居民收入增長幅度,2002—2010年連續(xù)9年城鄉(xiāng)人均收入比均保持在3∶1之上。”瑏瑧2002—2009年城鄉(xiāng)居民的收入具體數(shù)據(jù)見圖1。在2006年,有學者通過研究發(fā)現(xiàn),在農村內部,一個農民外出獲得的平均收入至少相當于八個依然留在農村從事農業(yè)生產的農民的純收入。瑏瑨城鄉(xiāng)收入差距是鄉(xiāng)村精英社會流動的一個重要驅動力,當今社會精英群體對自我能力與人生價值都有了清晰而明確的認知,這使得農民尤其是鄉(xiāng)村精英在面對城鄉(xiāng)收入的巨大差距時,選擇從鄉(xiāng)村到城市尋求自我的發(fā)展空間,實現(xiàn)自身利益與價值的最大化。
三、文化心理機制:城市迷思的強化與鄉(xiāng)土情結的弱化
鄉(xiāng)村精英流動也有著深刻的文化心理原因。在當前社會價值體系中,人們對城市—鄉(xiāng)村、農業(yè)—其他產業(yè)、農民—城市居民的認知,都有著濃厚的價值判斷色彩,農村代表著落后,城市代表著進步,“跳出農門”成為幾代農村人共同的夢想。所以,在基本政治架構與利益導向因素之外,“面子、政治理想以及生活習慣等因素都影響著人們的選擇”瑏瑩。所以,我們可以從農民傳統(tǒng)觀念對鄉(xiāng)村與城市的認知和判斷、農民對鄉(xiāng)村的情感依附與“鄉(xiāng)土情結”的弱化這兩個方面來加以分析,以深入把握當前鄉(xiāng)村精英社會流動的文化心理機制。
一方面,當前社會存在著“城市迷思”心理,這種由歷史與現(xiàn)實共同塑造的對城鄉(xiāng)根深蒂固的認識在短時期內難以改變。無論城市居民還是農民自身,往往把農村看成一個低度發(fā)展、文明程度不高、生活方式落后的區(qū)域———農村生產生活與農民身份成為中國人不得已而為之的一種底線選擇,是一種無法選擇之后的被動選擇。當然,這種心理的產生有著深刻的歷史背景。從工業(yè)革命開始,城市的發(fā)展與產業(yè)發(fā)展更緊密地聯(lián)系在一起,城市和鄉(xiāng)村的對峙與區(qū)域產業(yè)分布的差異成為一個事物的兩個方面。城市代表著最新科技與高度發(fā)達的生產力水平,這應當是一種現(xiàn)實狀態(tài)給人們帶來的觀感。在傳統(tǒng)中國,城鄉(xiāng)二元結構所體現(xiàn)出的主要特征是生產與生活方式的差異性,并未有十分明確的先進與落后之分。在特定的歷史時期,依托農業(yè)生產的鄉(xiāng)村往往表現(xiàn)得比城市更富庶與更有生存資料的保障,城市貧民往往處于比傳統(tǒng)農民更悲慘的境地。近代以來,戰(zhàn)亂與自然災害打破了中國鄉(xiāng)村的封閉性,鄉(xiāng)村中受到新文化教育的精英們開始走出鄉(xiāng)村,去城市尋求自己的發(fā)展,但鄉(xiāng)村中仍然存在著一個以農村地主與鄉(xiāng)紳為主體的精英群體,此時駐守鄉(xiāng)村生活并非是鄉(xiāng)村精英們迫不得已的選擇,而是一種基于自我價值判斷的理性選擇。
建國后,逐漸建立起來的制度再次用政治權力框定了城市和鄉(xiāng)村各自的存在體制。雖然在形式上兩個區(qū)域都建立起了完整的行政性生產組織———農村的大隊與城市的單位,在經濟發(fā)展水平上均由國家計劃下達,很難評估二者經濟發(fā)達程度的高低,甚至從某些方面看,有些富庶農村的農民生活比城市限額供應體系下的生活要寬裕得多。但是,這種體制卻通過賦予城市及其居民以諸多方面的特權,加深了人們對農村的貶值與對城市的青睞———城市對于農民而言,是一種難以企及的夢想,它代表著一種優(yōu)越身份與理想棲居之地。尤其是戶籍制度對于農民的種種限制,以及基于其上的種種城市特權,更加重了農民跳出農門的心理。當中國市場經濟建設的歷史時期到來時,城市借助于對現(xiàn)代科技、現(xiàn)代市場及資本優(yōu)勢,率先取得了經濟發(fā)展的巨大優(yōu)勢。而農村生產要素向現(xiàn)代市場經濟生產要素的轉變過程要復雜得多,尤其是土地作為核心生產要素,融入市場經濟程度不高,制約了農村經濟的快速發(fā)展。而改革開放后城市與農村經濟發(fā)展水平的巨大差異,更加重了自計劃經濟時期起便深深扎根于人們心中的“城市迷思”的文化心理定式———這種心理定式恰恰與美國學者湯普遜對城市的描述有相似之處,“城市的空氣使人自由”瑐瑠。另一方面,農民“鄉(xiāng)土情結”弱化,為其向其他地區(qū)和產業(yè)轉移奠定了心理基礎。在中國傳統(tǒng)社會的發(fā)展中,土地一直被看作整個社會的命脈,“安土重遷”是中國人固有的思維觀念。鄉(xiāng)土社會不但人口流動很小,土地也很少變動。正是傳統(tǒng)鄉(xiāng)村社會的封閉性與鄉(xiāng)村經濟的小農化,使得農民對土地產生心理上的依賴性與依附性,這種人身對土地的依賴與依附最終逐漸形成了農民們故土難離的“鄉(xiāng)土情結”。這種“鄉(xiāng)土情結”的弱化是改革開放后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以及新思維、新觀念的涌入二者合力的結果,市場經濟解放了農民對鄉(xiāng)村土地的人身依附,進而也消解了農民對土地心理依附的基礎。因此,我們應該清晰地認識到,除推動鄉(xiāng)村人群向城市流動的“城市迷思”情結之外,改革開放后社會政治經濟發(fā)展現(xiàn)實弱化了農民群體的“鄉(xiāng)土情結”,與“城市迷思”相對應的是人們對鄉(xiāng)村的拒斥心理,把鄉(xiāng)村視為落后、不發(fā)達、非現(xiàn)代化、迂腐等的誕生地。
這種農民“鄉(xiāng)土情結”的弱化與“城市迷思”的強化二力合一,最終形成推動鄉(xiāng)村精英社會流動的文化心理機制。憑借經驗觀察與理性分析可以發(fā)現(xiàn),中國鄉(xiāng)村面臨著空心化、勞動力老齡化與人口老齡化等諸多層面的社會問題。面對這些問題,學術界應該對簡單化的推動“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理論與實踐進行充分的檢討,明確鄉(xiāng)村優(yōu)勢勞動力與鄉(xiāng)村精英群體流失的社會現(xiàn)實。通過本文對鄉(xiāng)村精英流動內在機制的分析可以發(fā)現(xiàn),政治、經濟與文化三個層面均存在著鄉(xiāng)村精英社會流動的內在推動力,每個層面的推動力都有邏輯上的必然性。我們知道,只有留住現(xiàn)有鄉(xiāng)村精英,并吸引鄉(xiāng)村精英回流,重構鄉(xiāng)村精英群體,才能更好地建設農村,促進中國農村的長足穩(wěn)定發(fā)展。論者以為,欲重構鄉(xiāng)村合理的階層結構與鄉(xiāng)村主體的建設能力,應從以下三個方面著手:首先,在政治層面必須以制度體系建設為基點擴大鄉(xiāng)村治理機制中的精英容納力,避免鄉(xiāng)村自治中的小群體壟斷,再造鄉(xiāng)村精英的政治價值實現(xiàn)空間;其次,推動農村勞動力的理性轉移,加快城市社會承擔農村養(yǎng)老、農村教育的進程,并提高農業(yè)生產中的勞動力附加值,使之達到各產業(yè)平均的勞動力價值;最后,在逐漸消除城鄉(xiāng)政治經濟二元差異、為農村提供與城市均等的主要公共產品———道路、用水、住房、教育等的基礎上,利用鄉(xiāng)村生態(tài)優(yōu)勢,再造農民的鄉(xiāng)村認知,培育熱愛鄉(xiāng)村、保護鄉(xiāng)村、駐守鄉(xiāng)村的新時代的“鄉(xiāng)土情結”。
作者:張英魁曲翠潔單位:曲阜師范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