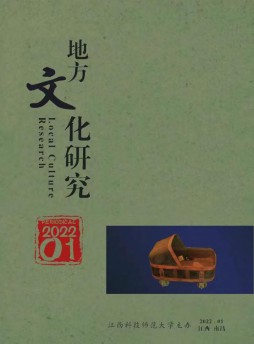地方民俗文化的移植與傳播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地方民俗文化的移植與傳播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摘要:發(fā)展民俗旅游是地方文化空間重塑的原動力之一,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民族文化的保護利用與傳播。以恩施土家女兒城作為分析對象,從文化空間生產的角度切入,審視地方民俗文化的移植與再生產問題,討論新的文化空間的形成、結構以及對民族文化傳播的影響。在女兒城的主題文化生產過程中,通過移植本土民俗文化資源,構建了新的文化空間,創(chuàng)造了一個新的土家民俗文化“凝視場域”,實現(xiàn)地方民俗文化“可參觀性”的再生產,推動了民族文化的共享性和多樣性發(fā)展,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延續(xù)鄉(xiāng)土記憶的文化空間。但必須警惕民族文化傳播過程中,由商業(yè)因素所導致的偽民俗現(xiàn)象對民族文化本真性的影響。
關鍵詞:文化空間;文化移植;文化傳播;文化資本;空間生產
“空間”原本是一個地理意義上的物理存在,將其引入社會研究后,這個概念就被賦予了一些新的意義,用來指代被人們有目的地生產出來的特定地域或地方。“文化空間”(culturalspace)作為專門術語,首先被用于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在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人類口頭及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宣言》(TheProclamationofMasterpiecesoftheOralandIntangibleHeritageofHumanity)中,文化空間被定義為“流行和傳統(tǒng)文化活動集中的場所”[1]。在我國有關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官方文件中,“文化空間”是一個時間性和空間性相統(tǒng)一的概念,強調在固定的時間和場所對傳統(tǒng)文化表現(xiàn)形式的集中展現(xiàn),因而既是一個視覺凝視場所,也是一種現(xiàn)實的文化保護實踐。在人類學中,“文化空間”的概念和范圍得到更大拓展,它強調有人類行為、時間觀念、歲時傳統(tǒng)或者人類本身的“在場”[2],包括物質生活、精神生活和社會生活等方方面面,成為文化人類學者考察文化生存與發(fā)展的一個重要視角。基于文化空間生產來考察地方民俗文化的移植與傳播,有助于我們深入理解當下伴隨著體驗經濟發(fā)展起來的地方文化資源開發(fā)利用的現(xiàn)實路徑。
一、民族文化空間生產的理論闡釋
時間和空間是民族文化生存與發(fā)展的基本形式。列斐伏爾(HenriLefebvre)的空間生產理論為我們討論少數(shù)民族文化的移植與傳播提供了重要的理論資源。在他看來,空間并不是單純的物質實體,而是社會實踐與社會結構相互作用的產物,“通過人類主體的有意識的活動而生成,社會空間產生于一定的社會生產模式,是一個社會過程的結果”[3]。在文化生產過程中,從一種生產方式轉換到另一種生產方式,必然伴隨著新空間的生產,列斐伏爾用“空間實踐”“空間表征”“表征空間”三個維度闡釋了空間生產所體現(xiàn)出的社會關系制造和物質生產過程。他把空間看作社會關系的載體,“空間里彌漫著社會關系,它不僅被社會關系支持,也生產社會關系和被社會關系所生產”[4]。因而空間的生產是一個關系化和過程化的動態(tài)范疇,我們不能脫離社會關系來討論空間問題。在列斐伏爾的三重性空間辯證法中,空間的三個維度是“共融的、互相作用的,是一種在真實和想象之間開放與重組的辯證互動關系”[5],文化可以通過這種不同維度的“空間再生產”得以維持自身的平衡和延續(xù)。在民俗文化資源開發(fā)過程中,投資者、地方政府、文化學者、發(fā)展專家等通過移植承載了傳統(tǒng)寓意的民俗活動,整合現(xiàn)代化、全球化因素,將傳統(tǒng)民俗符號化,建構出一個抽象的概念化空間,即“構想的空間”。而作為民族文化的承載人和詮釋者的當?shù)厝朔e極參與其中,通過物理意義上的空間活動生產著“可感知的空間”,保證了經濟和社會的生產與再生產,最終共同構建了一種以民族特色文化為主題的再現(xiàn)性空間,成為游客、投資人、創(chuàng)業(yè)者等共同使用的“生活的空間”,并使其具有了作為“地方”的內涵。由此可見,所謂“生產空間”,是一種涵蓋了時間、空間、體驗等復雜因素的文化實踐,再生產了一個地理空間、文化空間與社會空間疊加在一起的旅游主客體間互動的場域,其中折射出了文化、經濟、政治與權力結構之間的復雜交互作用。圍繞文化空間的生產與再生產,地方政府、投資者、旅游開發(fā)商、游客、當?shù)鼐用竦壤嬷黧w利用各自所擁有的象征資本,以旅游業(yè)為紐帶,在文化場域中進行著不同類型的資本交換和博弈,以各自的行動邏輯生產著民族文化,并以不同的話語符號來表達各自對文化空間的關注,形成了一個全新的空間關系格局。通過這些主體力量之間的社會交往,在“地方傳統(tǒng)”與“現(xiàn)展”的沖突和融合中不斷形塑著民族文化空間。當然,這種文化空間一旦形成,它又會成為一種現(xiàn)實的生產方式,作為一種生產資料和消費產品,作用于社會結構與社會關系的再生產,民族文化本身也在空間再生產運動中得到繼承、發(fā)展與傳播。目前,在全域旅游背景下,文化空間所根植的社會環(huán)境發(fā)生劇烈變化,各地結合自己的地域文化特色,發(fā)展文化旅游產業(yè),相繼打造本土文化旅游名片,生產出不同的地域文化空間。恩施女兒城就是通過對土家族傳統(tǒng)文化元素的移植、復制與重構,把具有地方性、民族性的文化根植進去,營造出新的民族文化景觀。這種“可參觀性”的再生產策略是什么,會對民族文化傳播產生何種影響等,厘清這些問題,可以為我們批判性地思考民族文化保護傳承與創(chuàng)新發(fā)展之間的復雜關系提供一種可能。
二、土家民俗文化空間的再生產策略
一般來說,少數(shù)民族民俗文化的自我生產是以民族的歷史積淀和文化的代際傳承為基礎的。在繁榮民族文化產業(yè)的文化發(fā)展策略和體驗經濟邏輯的強勢推動下,通過原生文化資源的再造,向我們展示出一幅重新組合和重新建構的民俗文化圖景。
(一)女兒城的文化空間再現(xiàn)1.自然空間的重建休閑旅游的發(fā)展推動了民族文化資源的開發(fā)利用,促進了民族旅游社區(qū)的重構,其中對傳統(tǒng)民族文化空間的保護和重建成為時下的一般路徑,傳統(tǒng)民俗旅游開發(fā)過程也是民族文化的再生產過程。有研究者認為,“遺產保護和旅游開發(fā)意義上的文化空間,應以遺產保護為核心,以文化氛圍營造為重點,同時需要現(xiàn)代產業(yè)意識的指導,是一個融合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具有體驗性和互動性的空間”[6]。女兒城遵循這一邏輯,由當?shù)赝顿Y商開發(fā)建設的土家族文化創(chuàng)意產業(yè)園,某種意義上也可算作文化旅游創(chuàng)新區(qū),致力于推動地方民族文化資源的產業(yè)化。該項目位于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占地一千余畝,主要以土家民俗文化為題材,結合文化旅游的需要進行資源重構,在視覺感知上契合土家民俗文化的外在表征,從宏觀布局到微觀細節(jié),都力求融入土家民俗文化元素,具有民族色彩的凝視物被建構。宏觀布局上,其建筑的整體規(guī)劃吸收了土家吊腳樓干欄式風格,凸顯了吊腳樓別致的形式與流動的視覺效果,從內到外把建筑技術美與藝術美相結合,展現(xiàn)了土家民居的文化內涵,但更注重審美的現(xiàn)代性和時代感。在對周邊環(huán)境的設計上,注重動靜結合、強調空間的均衡感。通過建筑物的設計、環(huán)境的營造建構了一種新的空間關系。微觀細節(jié)上力求處處體現(xiàn)土家民俗文化元素。各街區(qū)內的雕塑與環(huán)境有機結合,凝固了土家族人民日常生活的經典畫面。無論是挑擔的土家小伙和織錦的姑娘,還是澆鑄的耕牛和“畢茲卡大街”的雕塑,都述說著土家人的生活故事。臨街商鋪的裝飾也通過大紅燈籠、金黃玉米和鮮紅辣椒等突顯生活場景,再現(xiàn)土家民俗文化的日常生活細節(jié)。這些視覺符號被大量生產出來,制造了人們沉醉其中的視覺消費情境。從總體上看,就是按照視覺快樂原則,以物理空間為媒介,發(fā)揮物質因素在文化敘事中的功能和意義,通過物化空間的結構化、主題化實現(xiàn)了民俗文化的再生產,使其成為一個充滿意義的社會與文化實體,形成一個新的場所,并且注入了新的生產關系,將游客拉進一個充滿異域想象的視覺消費景觀中。2.人文空間的再造在空間生產理論中,空間與人文和物體密切聯(lián)系在一起,而文化空間是一種時空與人的活動相結合的文化的活態(tài)存續(xù),對其利用與保護,必須兼顧自然與人文兩方面,并將其作為一個整體進行集中呈現(xiàn)。在民俗文化資源的開發(fā)利用中,往往注重對民族文化所包含的歲時性的節(jié)日習俗、周期性的趕場貿易、季節(jié)性的情愛交流、娛樂性的歌舞盛會,以及族群性的文化歷史傳統(tǒng)等予以再現(xiàn),力求將文化空間中存在的多樣性時空結構與文化關系進行合理表述,使相互作用的旅游空間與生活空間共同依存于民族文化再生產空間結構中,在某種意義上讓再造的人文空間成為一個開放的“文化島”和符號空間。恩施女兒城的城名,實際上來自于被譽于東方情人節(jié)的“土家女兒會”這一區(qū)域性民族傳統(tǒng)婚俗文化———趕場相親,并且其作為重要的舞臺展演內容。每天為游客提供《趕場相親•女兒會》的大型實景演出,通過“女兒城娶媳婦”這一展演活動再現(xiàn)土家婚嫁習俗。主創(chuàng)人員把這一體現(xiàn)民族文化特質的民俗景觀重新進行視覺編碼,凸顯其觀賞性和視覺傳達性。女兒城整個街區(qū)的命名也體現(xiàn)出地方民俗文化特色,如“好吃街”“幺妹兒街”“畢茲卡大街”“耍耍街”“舍巴街”,每條街道的功能布局與其名稱內涵相對應,飲食、娛樂、購物、住宿、休閑一應俱全,既集中了散落在市井街巷的街區(qū)場景,又把帶有歲時性、周期性、季節(jié)性、娛樂性的民俗文化予以整體再現(xiàn)。在每條街道兩邊將當?shù)氐牡湫头窖杂枰哉故荆屚鈦碚吡私猱數(shù)夭糠秩粘I钫Z言的意義。除此之外,還為游客提供了參與性較強的土家人日常生活場景,如編草鞋、織西蘭卡普、烙豆皮、打糍粑、炕臘肉等,彰顯其原有的生活氣息,并賦予這些文化因素新的社會功能。通過“土家民俗博物館”將當?shù)赝良颐袼孜幕厣c歷史圖景勾勒出來,使動態(tài)文化、演示藝術、民俗行為與靜態(tài)的器物等有機結合,達到整體性敘事效果。所有這些文化要素都成為空間生產符號價值的原材料,在把握文化內部關聯(lián)性的基礎上,通過文化編碼重構,建構一個基于日常生活的、完整而真實的民俗文化空間,實現(xiàn)“可參觀性”的再生產,建構了一個“第二自然”,形成一個具有美學概念的現(xiàn)代土家民俗文化空間。
(二)民俗文化空間的再生產邏輯1.民俗旅游推動了文化資本化在列斐伏爾的空間生產理論中,空間生產機制是商品化和資本化的,空間的生產與其他同類商品的生產相似,“其目的是直接服務于資本的無限積累與擴張”[7]。在民俗文化空間再生產中,作為功能性概念的文化資本,雖不能直接進行量化交易,但它可以作為資本運作以發(fā)揮其類似于經濟資本的作用。[8]在當下的市場邏輯日益侵占日常生活空間的背景下,尤其是新旅游興起之后,少數(shù)民族民俗文化的“地方性”彰顯出了特別的意義和旺盛的生命力。而發(fā)展經濟與脫貧致富的主客觀需求進一步促進了文化資源的商品價值被重新審視,其旅游吸引力被深度挖掘。通常的路徑就是將民俗文化移植過來,重新包裝和表述之后,作為特殊的旅游吸引物來營銷,以創(chuàng)造出基于他者文化想象的旅游凝視,一步步推動文化的商品化。恩施女兒城坐擁如此豐富的土家文化資源,自然會努力挖掘與民俗文化相關聯(lián)的差異性特征來進行空間的再生產,把民俗文化作為一種值得體驗和維護的事物加以美學化和浪漫化,讓民俗文化空間成為可參觀、被消費的對象。其中的土家民俗博物館,不僅有三十多個民間老藝人常年駐館表演土家傳統(tǒng)藝術,而且還再現(xiàn)了打糍粑、烙豆皮、熏臘肉等土家民間傳統(tǒng)美食制作工藝。這些原本只屬于當?shù)厝说膱鏊唤M合起來,既作為土家民俗文化的展示場域,又成為游客參與體驗的消費場所,充分體現(xiàn)了再造的土家民俗文化空間在特色性、物理性、社會性、符號性與可消費性等特征上的高度統(tǒng)一。由此可見,文化一旦進入商品領域,融入消費空間的生產過程,其資本的邏輯必然凸顯,民俗文化便超越自身的意義產生了經濟價值,具有了民族文化產業(yè)與旅游產業(yè)融合發(fā)展的行業(yè)特征,產生與都市文化一樣的溢出效應。文化空間的生產推動了資本的增殖,而資本增殖又加快了空間生產的速度。2.消費主義加速了文化符號化現(xiàn)代社會是由消費主義主導的消費社會,所有事物都是可以被消費的對象,“產品的符號化成為消費社會產品的基本特征”[9]。民族文化的符號化是現(xiàn)代化和全球化共同作用的結果,隱含著全球化進程中的“地方依戀”[10],也是傳統(tǒng)的民族文化切入現(xiàn)代都市生活的一種方式,成為一種符號消費。在民族文化資源開發(fā)利用過程中,文化符號化實際上就是民俗空間再生產對少數(shù)民族傳統(tǒng)文化的移植、挪用和改造,使其能夠與大眾的現(xiàn)代審美達成共識。從某種意義上講,這既是對傳統(tǒng)的一種“繼承”,也是對傳統(tǒng)的一種“發(fā)明”,更是一種文化的再造。民俗本身是一種生活,是特定民族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文化符號化過程中,往往通過選擇有代表性的、地方性民俗文化元素,將其提煉成世俗的、易理解和傳播的符號,賦予其特定的文化身份,參與特定的文化空間建構,實現(xiàn)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的想象性對接,使民族文化得以象征性呈現(xiàn),進而滿足視覺消費的需要。傳統(tǒng)文化的審美意義作為符號被消費。土家女兒城以“土家女兒會”這一民俗為核心,把當?shù)赝良易鍌鹘y(tǒng)民俗文化中的審美進行了融合與重構,賦予其新的意義,被建構成一個想象性的、符號化的“相親之都、戀愛之城”。其他的文化元素,諸如傳統(tǒng)服飾、建筑結構、裝飾物品、特色工藝、民族飲食、歌舞藝術等,都從日常生活中剝離出來,融入符合當代審美情趣的因素,成為提取消費文化符號和文化空間生產的原材料,從功能到形態(tài),被加以改造、包裝,并給予了現(xiàn)代話語的闡釋和重構,被拼貼上時尚的標簽而獲得新的審美意義和功能。實際上,這些文化元素的重組和符號化都是為營造土家特色文化場所與彰顯土家女兒會這一民俗主題的文化表達服務。遵循這一空間生產機制和文化再生產邏輯,民俗傳統(tǒng)文化符號得以持續(xù)再生產。
三、文化空間再生產與民族文化傳播
任何傳統(tǒng)都會隨著社會發(fā)展被當代人不斷創(chuàng)造而發(fā)生變遷,但是這種變異后的新民俗往往需要經歷相當長的時間才可能得到認同,進而成為集體文化記憶被繼承和傳播。近年來日益興盛的民俗旅游,刺激了民俗文化的創(chuàng)造和再生產,地方政府和投資者挖掘民俗文化資源、制造民俗標志物、借用民俗外包裝進行文化空間生產與再生產,其中普遍存在“發(fā)明傳統(tǒng)”[11]的現(xiàn)象,特別是在歷經多維空間生產活動后,這種民俗文化空間會反過來影響置身其中的社會行動者的行為規(guī)范,社會關系、社區(qū)結構也會隨之變遷。那么,這種通過文化移植所進行的傳統(tǒng)再造對于民族文化傳播有什么樣的作用和意義呢?從客觀上講,“被發(fā)明的傳統(tǒng)”對民族文化傳播是有積極意義的。從各地民俗旅游景點的建設可以看出,傳統(tǒng)的發(fā)明主要是政府主導下的開發(fā)者行為,游客被視作旅游地的“現(xiàn)金流”,其興趣和熱情是“發(fā)明傳統(tǒng)”的原動力。但“地方文化是隱藏在平淡的日常生活中,缺乏吸引力”[12],民俗旅游的休閑和審美屬性又對“被展示的文化”提出了客觀需求,因而必須從日常生活中挖掘隱藏的“地方性”,制造出興奮點和差異性。從文化傳播層面來說,地理空間對傳播活動有較大影響。對游客而言,他們不可能長期融入文化原生地的日常生活去感受和體驗原生態(tài)異文化。那么這種帶有合成性的“發(fā)明的傳統(tǒng)”恰好從整體上為民族文化傳播生產了內容,把文化符號意義與旅游情景相融合,塑造了地方形象,重構了文化傳播空間,造就了便利的傳播條件和獨特的傳播方式,提高了民族文化傳播的效果。從主觀上看,盡管民俗學界對“傳統(tǒng)的發(fā)明”存在爭議,認為這種再造的文化傳統(tǒng)喪失了文化的“本真性”,將其視作“偽民俗”而大加批判,但對民族文化傳播而言,“發(fā)明的傳統(tǒng)”仍然具有促進傳播的作用,已然成為當下民族傳統(tǒng)文化現(xiàn)實生產方式。沒有文化的傳播,文化的保護、傳承與發(fā)展也無從談起。對再造的傳統(tǒng)文化的本真性的質疑,實際上反映的是學者、游客、投資者和文化持有人對待民俗的出發(fā)點不同。雖然被展示的民俗很多時候是對傳統(tǒng)民俗的改造和創(chuàng)造性的再生產,但這種舞臺化展演只要不是胡編亂造,而是依據(jù)一定的地方文脈,選取地方文化傳統(tǒng)元素,符合地方文化特征的合理化想象與重構,這種文化空間的再生產就能夠對傳統(tǒng)的價值產生強化作用,有助于民族文化的傳承、發(fā)展。況且民俗的發(fā)展本身就是一個建構與發(fā)明的過程,“需要被后人不斷地闡釋與再闡釋才能產生真正的文化生命力”[13],只有能夠改變文化擁有人和詮釋者生活境遇,為現(xiàn)實的民族發(fā)展提供動力的傳統(tǒng)文化才能真正喚起當?shù)厝说奈幕杂X和文化自信,從而激發(fā)當?shù)孛癖娭鲃又匾晫鹘y(tǒng)習俗的提煉、保護和發(fā)展,激活他們的文化創(chuàng)造力。從民俗文化空間的生產方式來看,土家女兒城屬于典型的創(chuàng)新復合式生產,其依托當?shù)馗患纳贁?shù)民族傳統(tǒng)文化資源,通過綜合利用多種旅游開發(fā)模式,借助于文化的借用,發(fā)明和激活傳統(tǒng),主要以起源于恩施石灰窯一帶的土家“女兒會”這一典型的民俗文化為焦點,對當?shù)赝良胰巳粘I畹膱鼍昂推芜M行融合與重組,建構起一個全新的地理空間、文化景觀和民俗空間,集中體現(xiàn)地方民俗文化精髓,使空間具有了文化功能和傳播功能。這種民俗仿制和文化移植看似破壞了地方民族文化,實際上促進了日漸式微的傳統(tǒng)的復興。在此文化空間內部,投資者、當?shù)厝恕⒂慰偷刃袨橹黧w積極進行頻繁的社會互動,獲得共享的意義,共同參與對民族文化歷史的想象與敘述。在這里,突破了文化傳播活動與日常生活的界限,空間內的社會結構與文化關系被不斷地再生產,自然空間、文化空間、生活空間與傳播空間疊加在一起,營造了一種全息的文化傳播環(huán)境。而作為民俗文化消費者和欣賞者的游客群體,其空間移動和自媒體傳播所引起的文化擴散,使其成為文化生發(fā)地、保存地到文化擴散地的中介,他們的空間移動過程也就是文化傳播的過程。同時,在旅游扶貧和振興地方文化產業(yè)的背景下,現(xiàn)代傳媒對土家女兒城的宣傳、報道,進一步擴大了這一文化空間的影響力和傳播力,為民族文化生產了更廣泛的虛擬體驗空間和信息傳播空間。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傳統(tǒng)的發(fā)明”盡管是為了迎合“旅游凝視”的需要和追求旅游經濟效益,但在客觀上的確推動了民族文化的傳承,有益于地方經濟和社會發(fā)展。
四、必須警惕“偽民俗”對民族傳統(tǒng)文化的沖擊
“民族文化是一個民族的靈魂,是一個民族在千百年來的歷史中逐漸形成的。民族文化的恢復與移植要尊重民族的傳統(tǒng)和歷史。”[14]在文化空間的重構中,“傳統(tǒng)的發(fā)明”原本只是一種現(xiàn)象描述,并不包含價值判斷,但隨著全球化和現(xiàn)代化進程的加快,“傳統(tǒng)的發(fā)明”呈現(xiàn)出一種極端化傾向,遠離日常生活、遠離本土的雜糅性文化空間被制造出來,將不同地域和族群的傳統(tǒng)進行機械拼湊、簡單組合,迎合他者的獵奇心理,以招徠游客。把文化事象與其生產空間割裂開來,純粹追求搭文化的臺,唱經濟的戲。這種歪曲歷史傳統(tǒng)、曲解文化元素的“去生活化”的民俗空間再生產,必須引起政府、文化資源開發(fā)和投資者、文化研究的專家學者和當?shù)厝说母叨戎匾暋km然不要過分苛求文化空間再生產中的本真性,但對毫無章法、過猶不及的“偽民俗”不加糾正,任其野蠻生長、自由發(fā)展,表面上貌似實現(xiàn)了文化事象的復活與放大,實際上卻可能造成社會公眾對民俗文化事象的信任危機,對地方民俗文化而言是一種“創(chuàng)造性破壞”,使少數(shù)民族傳統(tǒng)文化陷入污名化的泥潭,勢必會對社會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帶來不良影響,隱含著極大的社會文化風險。土家女兒城作為恩施旅游的一張名片和文化地標,事實上已經成為恩施土家族文化傳播的重要場所。但是,當其一旦成長為比較成熟的休閑旅游目的地之后,仍然沒有擺脫國內其他同類文化空間再生產的窠臼。盡管努力遵循“傳統(tǒng)文化為基,新興文化為表”的文化再生產路徑,但在實際的文化空間再生產中,一定程度上還是未能避免形式上的“再地方化”與內容上的“去地方化”,混合文化嵌套并存的問題逐漸顯現(xiàn)出來,勢必會對精心重構的“土家女兒會”新民俗帶來一定程度的消解,在一定程度上動搖了文化旅游活動可持續(xù)發(fā)展的根基。因此,在民族傳統(tǒng)文化資源開發(fā)利用中,一定要闡釋清楚不同的文化層次之間、不同的文化事象之間的互動、互生與互滲關系,重視文化符號的可理解性,適度控制旅游空間與生活空間的邊界,把握好仿造生產的度,切不可粗制濫造、嘩眾取寵,必須要深入挖掘民族文化的深層內涵,使物質文化的“形”與非物質文化的“神”高度統(tǒng)一,做到形神兼?zhèn)洌ㄟ^提升文化空間的內涵,從而產生邊際效用遞增的效應。五、結語土家女兒城的建造在本質上是文化空間的再生產行為,隱藏了深層次的社會生活與文化結構變遷。在這個再造的文化空間里,有對土家文化的創(chuàng)新,也有對土家文化的堅守。這種文化空間生產既是經濟資本運行邏輯作用的結果,也是一種土家族文化保護與傳承的戰(zhàn)略選擇。但其發(fā)展模式告訴我們,在民族文化的移植與傳播過程中,對民俗文化資源的開發(fā)必須把握好價值坐標問題,在厘清傳統(tǒng)民俗文化事象的地位、性質、特點和作用之后,對傳統(tǒng)民俗文化進行科學的現(xiàn)代闡釋和適度開發(fā),既要尊重歷史、尊重生活,還原真實的民俗場景,又必須在文化品牌打造與民族文化空間元素重組上力求平衡,避免斷章取義,切忌簡單的文化符號化生產,而是需要完成深層次的文化重構,防止對民族文化本真性的誤讀和丟失。在保護中開發(fā),在開發(fā)中保護,真正實現(xiàn)民族文化傳播和民族生態(tài)保護的高度統(tǒng)一,努力追求文化建構與市場績效的雙贏,從而真正促進民族文化的自我更新與超越。總之,在文化資源的開發(fā)利用中,如何堅守民族文化的獨立性、傳承性和傳播的方向性,使文化得到平衡發(fā)展和穩(wěn)定延續(xù),這是政府、投資商、文化研究者需要進一步探索和研究的重要課題。
作者:譚華;鄭巧 單位:湖北民族學院
擴展閱讀
- 1地方債務審計
- 2地方債券
- 3地方財政職能
- 4地方債務成因剖析
- 5地方財政對策
- 6地方土地集約運用評析
- 7地方消費環(huán)境
- 8地方會計管理簡介
- 9地方食品安全報告
- 10發(fā)行地方公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