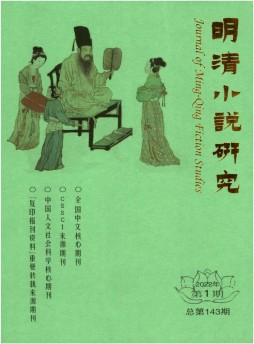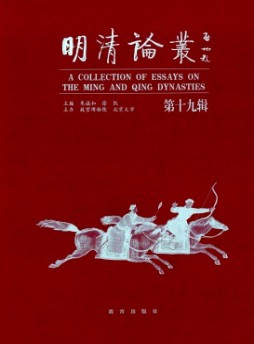明清文學(xué)文化文學(xué)批評(píng)論文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zhǔn)備了明清文學(xué)文化文學(xué)批評(píng)論文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diǎn)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xiě)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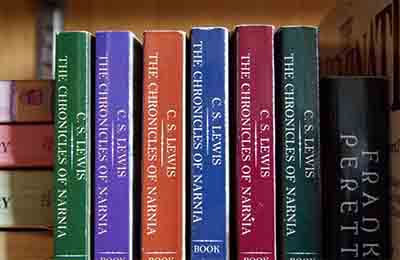
一、以“險(xiǎn)”構(gòu)詩(shī)歌奇境
明清詩(shī)學(xué)對(duì)于以“險(xiǎn)”構(gòu)詩(shī)歌奇境,有更為明確的論述。明末清初冒襄《杜少陵夔州詩(shī)選序》說(shuō):“夫不奇則非殊勝,不險(xiǎn)則不奇,不僻則不險(xiǎn),人境文境詩(shī)境無(wú)不比然。”[3](P564)詩(shī)歌不險(xiǎn)則不奇,“險(xiǎn)”可以構(gòu)奇境,詩(shī)文皆然。清代金堡《陳彥達(dá)詩(shī)集序》也說(shuō)“:情交于境而發(fā)為詩(shī),情不極其郁勃?jiǎng)t詩(shī)不奇,境不極危且險(xiǎn)則情不郁勃。”[4](P399)金堡直指詩(shī)歌境險(xiǎn),才能出奇詩(shī)。從具體的詩(shī)歌批評(píng)來(lái)看,明清詩(shī)學(xué)標(biāo)舉了“險(xiǎn)”對(duì)于建構(gòu)詩(shī)歌奇境的意義。明代陸時(shí)雍《詩(shī)鏡總論》說(shuō)“:司空曙……‘窮水云同穴,過(guò)僧虎共林’,昔庾子山曾有‘人禽或?qū)Τ病洌淦嫒ね纵^險(xiǎn)也。凡異想異境,其托胎處固已遠(yuǎn)矣。”[5](P1418-1419)司空曙《送曹三同猗遊山寺》“窮水云同穴,過(guò)僧虎共林”所展現(xiàn)的意境與庾信《園庭詩(shī)》“樵隱恒同路,人禽或?qū)Τ病毕嗨疲仔旁?shī)歌更“險(xiǎn)”,就奇境而言,超過(guò)司空曙詩(shī)歌。清代法式善《梧門詩(shī)話》“:袁子才令陜西,日登華山。《青柯坪詩(shī)》云:‘白日死崖上,黃河生樹(shù)梢。’奇境奇語(yǔ),可與孟東野‘南山塞天地,日月石上生’句并傳。”[6](P53)詩(shī)歌以死、生指稱白日、黃河,極“險(xiǎn)”,故法式善稱之為“奇境奇語(yǔ)”。以“險(xiǎn)”構(gòu)詩(shī)歌奇境,亦有一定限度。清代賀貽孫《詩(shī)筏》指出:蘇子由云:“子瞻文奇,吾文但穩(wěn)。吾詩(shī)亦然。”此子由極謙退語(yǔ)。然余謂詩(shī)文奇難矣,奇而穩(wěn)尤難。南威、西施,亦猶人也,不過(guò)耳目口鼻,天然勻稱,增之一分則太長(zhǎng),減之一分則太短,便是絕色。諸葛武侯老吏謂桓溫曰:“諸葛公無(wú)他長(zhǎng),但事事停當(dāng)而已。”殷浩閱內(nèi)典嘆曰“:此理只在阿堵邊。”后代詩(shī)文名家,非無(wú)奇境,然苦不穩(wěn),不勻稱,不停當(dāng),不在阿堵邊。[7](P140)詩(shī)歌之“險(xiǎn)”與“穩(wěn)”本是相對(duì)的,但亦應(yīng)辯證結(jié)合,正如“奇”與“正”相對(duì),亦要相輔相成。以“險(xiǎn)”造詩(shī)歌奇境,同時(shí)要達(dá)到“奇而穩(wěn)”。有奇境而不穩(wěn)當(dāng),則落入下乘之境。詩(shī)歌之“險(xiǎn)”并非生搬硬造,應(yīng)該是遇境而生。以“險(xiǎn)”構(gòu)詩(shī)歌奇境,亦要求得自然。明代李日華《紫桃軒又綴》卷三說(shuō):立言必貴典雅坦明,即有奇險(xiǎn),亦遇境而生,非強(qiáng)鑿所就,自然行遠(yuǎn)。揚(yáng)雄《法言》《太玄》,至今在傳不傳間。若唐盧殷之文千余篇,李礎(chǔ)之詩(shī)八百篇,樊紹述著《樊子書(shū)》六十卷,雜文九百余篇,皆不傳,以其艱深晦塞,縱有奇,非人情所通好故也。[8](P97)李日華主張奇險(xiǎn)要“遇境而生”,不可強(qiáng)鑿而就。他指出盧殷、李礎(chǔ)、樊紹述的詩(shī)文正因?yàn)檫^(guò)于奇險(xiǎn),艱深晦塞,以至于不傳于后世。明代瞿佑《歸田詩(shī)話》也說(shuō)“:戴式之嘗見(jiàn)夕照映山,峰巒重疊,得句云‘夕陽(yáng)山外山。’自以為奇,欲以‘塵世夢(mèng)中夢(mèng)’對(duì)之,而不愜意。后行村中,春雨方霽,行潦縱橫,得‘春水渡傍渡’之句以對(duì),上下始相稱。然須實(shí)歷此境,方見(jiàn)其奇妙。”[9](P24-25)詩(shī)人實(shí)歷奇境而造詩(shī)歌奇境,才能見(jiàn)其奇妙,才能奇得自然。
二、以“變”構(gòu)文章奇境
“奇境”與“正境”相對(duì),文章奇境主要通過(guò)“變”的方式構(gòu)境。王葆心《古文詞通義》卷九“:包世臣稱讀文之境所見(jiàn)有遷變,故作文之境亦自有遷變,文家公例,莫不如是。明清文學(xué)蓋必有變境始有進(jìn)步。”[10](P7493)作文之境有遷變,這是文家的公例,只有變境,作文才能進(jìn)步。文章不變則庸腐,只有“變”才能令人耳目一新,開(kāi)辟出奇境。清代呂留良《呂晚邨先生論文匯鈔》說(shuō)“:昔人論作文,只是一個(gè)翻案法耳,此說(shuō)甚淺,然議論文字須用此法,乃有奇境開(kāi)辟。盡將從前呫嗶璅說(shuō)翻駁一新,拔趙幟而立漢幟,固非辣手不辦。”[10](P3345)翻案法是文章之“變”,它脫出窠臼,出人意料,故而能開(kāi)出奇境。文似看山不喜平,故呂留良《呂晚邨先生論文匯鈔》又說(shuō)“:山無(wú)峰巒起伏,即為頑山;水無(wú)波瀾蕩洄,即成死水。文章佳境,亦只在起伏蕩洄處得意耳。”[10](P3347)山水無(wú)變化,則無(wú)靈性,文章亦如此。文章的佳境、奇境,只有通過(guò)起伏蕩洄之變,方能達(dá)到。同樣是以山水喻文,吳曾祺《涵芬樓文談》則說(shuō):大凡文之至者,境以奇險(xiǎn)峭拔為勝,音以激切凄戾為工。譬之言山者,峰巒聳拔,壁立千仞,而委迤綿亙者,無(wú)足言也;言水者,湍流激射,一瀉千里,而溁洄蕩漾者,無(wú)可言也。蓋必如此而后使人驚嘆駭絕,心魄俱震。彼夫臺(tái)閣之文,舂容大雅,淵然金石,以之歌詠太平,自見(jiàn)洋洋盈耳,然試與之究世故之險(xiǎn)巇,狀人情之變幻,則有不及喻者矣。獨(dú)有逐臣羈客、勞人思婦,心思所極,窮無(wú)復(fù)之,而閱歷既久,智力漸生,無(wú)所發(fā)泄,一切托之于文章,離怪惝怳,神與之通,往往非人力所能至。吳曾祺推崇文章奇境,認(rèn)為至文“境以奇險(xiǎn)峭拔為勝”,這就好比高山以聳拔陡峭為勝,流水以湍流激射為勝,如此才能令人驚嘆駭絕。而文章奇境,需要通過(guò)“狀人情之變幻”來(lái)達(dá)到,這也是主張以“變”構(gòu)奇境。從具體的文章品評(píng)來(lái)看,明清以來(lái)的文章批評(píng)強(qiáng)調(diào)以“變”構(gòu)奇境。比如,《孟子》長(zhǎng)于論辯,其中有“變”。《孟子·梁惠王下》: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內(nèi)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清代方宗誠(chéng)《論文章本原》卷三評(píng)論此段說(shuō):“‘王之臣’章,亦書(shū)說(shuō)體也。‘四境之內(nèi)不治’是主意,卻含蓄不先說(shuō)出。首段起得飄忽,令王不測(cè)其意。次段從對(duì)面刺入,亦令王不測(cè)。三段忽上正面,令王無(wú)從嚲閃,亦奇幻不測(cè)。‘王顧左右而言他’,忽然放開(kāi),又令人不測(cè)。此章文境,最奇縱變化。”[10](P5669-5670)孟子要批評(píng)齊宣王治國(guó)無(wú)方,卻不先說(shuō),而先從友之不可托、士師不治士說(shuō)起,令齊宣王不測(cè)其意,入其甕中,最后以“四境之內(nèi)不治”批評(píng)齊宣王,以至其無(wú)言以對(duì)。方宗誠(chéng)認(rèn)為這種文境最是奇縱變化。《孟子》中類似之處頗多,又比如方宗誠(chéng)評(píng)論《孟子·公孫丑上》:“此章至‘圣人復(fù)起,必從吾言’,意已盡矣,下復(fù)作一大翻瀾,文境更闊,廣引諸賢,以配前段,廣引諸子,中間多少波瀾,文境奇肆之至。”[10](P5673)這是以“文境奇肆”評(píng)價(jià)《孟子》波瀾起伏多變。韓愈古文有新創(chuàng),《送孟東野序》用三十八個(gè)“鳴”字,參差變換,文境奇崛。唐文治《國(guó)文經(jīng)緯貫通大義》評(píng)論說(shuō)“:用三十八‘鳴’字,參差錯(cuò)落,處處變換,文境如雷電風(fēng)云,一時(shí)并作,又如百川歸海,萬(wàn)派朝宗,可謂神乎技矣。”[10](P8283)這正指出韓文“處處變換”的特點(diǎn),如此則文境必奇。王葆心《古文詞通義》卷六也說(shuō)“:非盡百家之美不成一人之奇,非取法最高之境不能開(kāi)獨(dú)造之域。此惟韓退之能知之,宋以下皆不講也。”[10](P7325)他對(duì)韓愈古文之奇境評(píng)價(jià)頗高。蘇軾的四六矯變,擺脫了隋唐五代的拘囿,開(kāi)辟出了奇境。清代孫梅《四六叢話》評(píng)價(jià)說(shuō)“:東坡四六,工麗絕倫中筆力矯變,有意擺落隋唐五季蹊徑。以四六觀之,則獨(dú)辟異境;以古文觀之,則故是本色,所以奇也。”[10](P4966)孫梅指出蘇軾四六正是以“矯變”來(lái)“獨(dú)辟異境”。文章固然以“變”構(gòu)奇境,但文章之“變”也要遵循一定的規(guī)矩。呂留良《呂晚邨先生論文匯鈔》指出“:一題眾拈變格,勢(shì)所必至。但變而仍當(dāng)于理法,正是文人弄奇,妙境無(wú)窮處,如不當(dāng)于理法,雖正格無(wú)益也。”[10](P3356)文章“變”是大勢(shì)所趨,文人弄奇,妙境無(wú)窮,但不能違于理法,否則無(wú)益于文章。
三、以“幻”構(gòu)小說(shuō)戲曲奇境
小說(shuō)、戲曲這類敘事文體中的奇境,不同于詩(shī)文以抒情、議論為特點(diǎn)的奇境,其奇境主要通過(guò)“幻”來(lái)獲得。小說(shuō)是想象、虛構(gòu)的產(chǎn)物,其特點(diǎn)之一就是“幻”。由“幻”而構(gòu)小說(shuō)奇境,這是小說(shuō)創(chuàng)作中的常態(tài)。清代瀟湘館侍者《澆愁集自敘》說(shuō):“《 洞冥》亦是寓言,《莊》《騷》半多托興。非非想處,即現(xiàn)天宮;種種光中,別開(kāi)世界。每意來(lái)而境造,當(dāng)情至而文生。”對(duì)于小說(shuō)家而言,“彈指而現(xiàn)化城,刻骨而摹幻相”,這是他們構(gòu)造小說(shuō)情景的基本能力。清代王韜《淞隱續(xù)錄自序》 指出,志怪小說(shuō)中的奇境幻遇,自成一世界,不必真有其事。他說(shuō):心能入乎境之中,而超乎境之外,且能憑虛造為奇境幻遇以自?shī)势湫摹!駥⒂谥T蟲(chóng)豸中,別辟一世界,構(gòu)為奇境幻遇,俾傳于世。非筆足以達(dá)之,實(shí)從吾一心而之所生。自來(lái)說(shuō)鬼之東坡,談狐之南董,搜神之干寶,述仙之曼卿,非必有是地有是事,悉幻焉而已矣。幻由心造,則人心為最奇也。小說(shuō)的文體特點(diǎn)之一就是“幻”,以虛構(gòu)的方式可以創(chuàng)造小說(shuō)奇境。而“幻”是人心創(chuàng)造的,小說(shuō)奇境說(shuō)到底就是人的奇情的反映。清代姬金麟《六合內(nèi)外瑣言序》也說(shuō):“情至生文,意來(lái)造境,問(wèn)天有對(duì),漱地成形。即此塵塵念念之因,無(wú)非怪怪奇奇之事。”小說(shuō)奇境的生成,是小說(shuō)虛構(gòu)性特點(diǎn)的反映,更是與小說(shuō)作者的奇情奇意緊密相聯(lián)。從小說(shuō)評(píng)點(diǎn)來(lái)看,小說(shuō)“奇境”往往指稱異特不凡的場(chǎng)景,它對(duì)于小說(shuō)情節(jié)的發(fā)展,具有重要的推動(dòng)作用。比如《三國(guó)演義》第三十五回“玄德南漳逢隱淪,單福新野遇英主”寫(xiě)道“:卻說(shuō)玄德躍馬過(guò)溪,似醉如癡,想:‘此闊澗一躍而過(guò),豈非天意!’迤邐望南漳策馬而行,日將沉西。正行之間,見(jiàn)一牧童跨于牛背上,口吹短笛而來(lái)。”清初小說(shuō)評(píng)點(diǎn)家毛宗崗?qiáng)A評(píng):“忽然別出奇境。”又比如《水滸傳》第四十一回“還道村受三卷天書(shū),宋公明遇九天玄女”寫(xiě)宋江返家,趙能、趙得率兵追捕宋江。是夜,月色朦朧,路不分明,宋江只顧揀僻靜小路去處走。約莫也走了一個(gè)更次,只聽(tīng)得背后有人發(fā)喊起來(lái)。宋江回頭聽(tīng)時(shí),只隔一二里路,看見(jiàn)一簇火把照亮,只聽(tīng)得叫道:“宋江休走!”宋江一頭走,一面肚里尋思“:不聽(tīng)晁蓋之言,果有今日之禍,皇天可憐,垂救宋江則個(gè)。”遠(yuǎn)遠(yuǎn)望見(jiàn)一個(gè)去處,只顧走。少間風(fēng)掃薄云,現(xiàn)出那輪明月,宋江方才認(rèn)得仔細(xì),叫聲苦,不知高低。看了那個(gè)去處,有名喚做還道村。前寫(xiě)月色朦朧,路不分明,后寫(xiě)風(fēng)掃薄云,現(xiàn)出明月。月暗、月明,呈現(xiàn)出不同的場(chǎng)景。明末清初文學(xué)批評(píng)家金圣嘆夾批:“寫(xiě)得妙。月暗月明,翻入奇境。”上述兩例均是以虛構(gòu)的奇境推動(dòng)小說(shuō)情節(jié)的發(fā)展,而這些“奇境”并不是怪俶詭幻,它們?cè)谛≌f(shuō)的整體結(jié)構(gòu)中呈現(xiàn)為突然而至的平常情景,它們是因突然而“奇”,并非因詭怪而“奇”。正如清代許道基《原李耳載序》評(píng)論小說(shuō)源流時(shí)所指出:“夫天下之奇,不在奇事在常事,且在常理。鯨吆鰲擲,牛魅蛇怪,為味轉(zhuǎn)淺。”這種視“目前常事,轉(zhuǎn)出奇境”為天下之至奇的觀點(diǎn),顯然代表了明清小說(shuō)批評(píng)對(duì)于奇境的基本審美趣味。當(dāng)然,這種目前常事,皆是虛構(gòu)的結(jié)果,它體現(xiàn)出虛幻而不失于藝術(shù)真實(shí)的特點(diǎn)。戲曲奇境也是由“幻”而造,亦是強(qiáng)調(diào)幻不失真。明末清初戲曲家袁于令《焚香記序》說(shuō):茲傳之總評(píng),惟以“真”字足以盡之耳。何也?桂英守節(jié)、王魁辭姻無(wú)論,即金壘之好色,謝媽之愛(ài)財(cái),無(wú)一不真。所以曲盡人間世炎涼喧寂景狀,令周郎掩泣,而童叟村媼亦從而和之,良有以已。然又有幾段奇境,不可不知。其始也,落魄萊城,遇風(fēng)鑒操斧,一奇也;及所聯(lián)之配,又屬青樓,青樓而復(fù)出于閨幃,又一奇也。新婚設(shè)誓,奇矣;而金壘套書(shū),致兩人生而死,死而生,復(fù)有虛訃之傳,愈出愈奇。悲歡杳見(jiàn),離合環(huán)生。讀至卷盡,如長(zhǎng)江怒濤,上涌下溜,突兀起伏,不可測(cè)識(shí),真文情之極其紆曲者,可概以院本目之乎?袁于令所謂戲曲之“真”即藝術(shù)真實(shí)之意。《焚香記》中,桂英守節(jié)、王魁辭姻、金壘好色、謝媽愛(ài)財(cái),這些情節(jié)都是提煉人世間存在的事件并經(jīng)過(guò)藝術(shù)加工而成。《焚香記》有四段奇境:一是落魄萊城,遇風(fēng)鑒操斧;二是所聯(lián)之配屬青樓而復(fù)出于閨幃;三是新婚設(shè)誓;四是生而死,死而生。這四段奇境一方面體現(xiàn)出戲曲敘事的虛構(gòu)性特點(diǎn),另一方面又體現(xiàn)出戲曲結(jié)構(gòu)的突轉(zhuǎn)性特點(diǎn)。戲曲奇境縱然虛幻,然亦不失于藝術(shù)真實(shí)。明末戲曲家王思任《西廂記序》指出了戲曲之奇對(duì)于戲曲傳播的意義,所謂“事不奇不傳,傳其奇而詞不能肖其奇,傳亦不傳”,又指出戲曲之奇必須達(dá)到藝術(shù)真實(shí),虛構(gòu)的事件場(chǎng)景,要達(dá)到“起當(dāng)場(chǎng)之骨,一一呵活眼前”的效果,才能真正傳之后世。這需要戲曲家具有“無(wú)中造有”的出眾藝術(shù)才能。戲曲亦是強(qiáng)調(diào)從目前常事,轉(zhuǎn)出奇境。王思任所謂“本一常境,經(jīng)之即奇”,即是此意。樸齋主人也說(shuō):“是劇結(jié)構(gòu)離奇,熔鑄工煉,掃除一切窠臼,向從來(lái)作者搜尋不到處,另辟一境,可謂奇之極、新之至矣!然其所謂奇者,皆理之極平;新者,皆事之常有。”家常事中有大量的戲曲素材可供參演,李漁《風(fēng)箏誤》之奇體現(xiàn)在結(jié)構(gòu)上,掃除窠臼,另辟一境,并不是牛鬼蛇神之奇。綜上,明清文學(xué)批評(píng)對(duì)于詩(shī)、文、小說(shuō)、戲曲的構(gòu)境之途有深入探討,概括來(lái)說(shuō),詩(shī)歌以“險(xiǎn)”構(gòu)奇境,文章以“變”構(gòu)奇境,小說(shuō)戲曲以“幻”構(gòu)奇境。這些理論概括,體現(xiàn)了不同文體在構(gòu)境上的迥異特點(diǎn)。詩(shī)歌之險(xiǎn)要不悖于自然,文章之變要合于理法,小說(shuō)戲曲之幻要不失于藝術(shù)真實(shí)。這些主張又反映出明清文學(xué)批評(píng)在構(gòu)境上的獨(dú)特審美趣味,其中所揭示的規(guī)律性、真理性的內(nèi)涵,具有超越時(shí)代的普適性,對(duì)于今天的文學(xué)構(gòu)境而言,依然具有理論生命力。
作者:陳玉強(qiáng)單位:河北大學(xué)文學(xu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