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文學(xué)思考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zhǔn)備了左翼文學(xué)思考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diǎn)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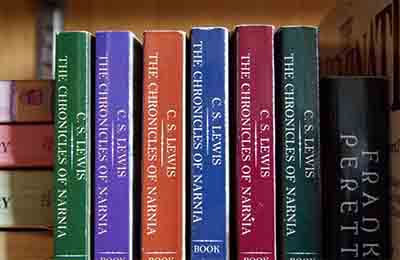
【內(nèi)容提要】
關(guān)于重新審視左翼文學(xué)運(yùn)動(dòng)的歷史作用及其經(jīng)驗(yàn)教訓(xùn),本文并沒有直接闡釋,而是從左翼作家中的最重要的一位人物魯迅的個(gè)人體驗(yàn)中來進(jìn)行考察和探討的。這里所說的“個(gè)人體驗(yàn)”,首先注重的就是當(dāng)事人的第一手資料,以史料來說話、以最客觀的事實(shí)來作結(jié)論。文章內(nèi)含有兩個(gè)部分,即以新文學(xué)運(yùn)動(dòng)和左翼文學(xué)運(yùn)動(dòng)這兩個(gè)時(shí)期來進(jìn)行分析和互相觀照。前一部分以《新青年》團(tuán)體為中心,分析了《新青年》同人之間的關(guān)系,特別是陳獨(dú)秀與胡適、魯迅與陳獨(dú)秀及胡適之間的關(guān)系,由此而認(rèn)識(shí)到新文學(xué)運(yùn)動(dòng)本質(zhì)上是屬于文藝復(fù)興性質(zhì)的思想啟蒙運(yùn)動(dòng),而并不宜納入純粹的政治斗爭的范疇之中。文章后一部分,從“左聯(lián)”的建立直到解散始終存在內(nèi)耗甚至是殘酷斗爭的危機(jī)這一事實(shí)來進(jìn)行分析,說明了:作為一個(gè)政黨外圍組織性質(zhì)的文學(xué)團(tuán)體,它其實(shí)是沒有承當(dāng)文學(xué)革命與思想啟蒙的任務(wù)的;因此,它并不能在真正意義上促進(jìn)文學(xué)運(yùn)動(dòng)向前發(fā)展。
【關(guān)鍵詞】左翼文學(xué)/《新青年》/陳獨(dú)秀/胡適/魯迅/“左聯(lián)”
每讀《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這篇未完稿都使人感到無限的惋惜,這篇回憶正待展開,也許只差一天的工夫就可寫完,可是意想不到的是,他的肺病急性發(fā)作了,更意想不到的是,由于一個(gè)日本醫(yī)生的耽擱,——這個(gè)日本醫(yī)生在束手無策的情況下甚至根本沒有考慮讓家屬及時(shí)送他到醫(yī)院采取合理的搶救措施,嚴(yán)重的失職,延誤了病情,因而導(dǎo)致極其嚴(yán)重的后果,發(fā)生了無法挽救的不幸事情。他的突然去世,并不只是中斷了一篇文章或一本書的寫作,而是過早的中止了一位20世紀(jì)中國最杰出的作家一生的事業(yè),尤其是當(dāng)他正由一個(gè)邊緣作家開始向純文學(xué)回歸之時(shí),就尤為可惜。他的遺孀許廣平整理他的遺著時(shí)說,有幾篇文章他是另外單獨(dú)放在一邊的,這就是:《半夏小集》、《“這也是生活”……》、《死》、《女吊》(見《且介亭雜文末編·后記》)。這是一組《野草》、《朝花夕拾》性質(zhì)的散文作品,他生前計(jì)劃還要陸續(xù)寫出一些,準(zhǔn)備再編一本散文集或一本回憶錄的,他跟馮雪峰就說過這個(gè)意思。魯迅除了把《半夏小集》等4篇散文另擱一邊之外,很明顯還有一篇回憶散文他是沒有放在待編的《且介亭雜文末編》里的,這就是:《我的第一個(gè)師父》。這一篇回憶散文發(fā)表在剛剛在上海創(chuàng)刊的他的友人孟十還編輯的《作家》月刊的創(chuàng)刊號(hào)上。此刊的第2期接著發(fā)表了《〈出關(guān)〉的“關(guān)”》,第5期上又發(fā)表了他在左翼文學(xué)運(yùn)動(dòng)中的最后一篇論戰(zhàn)文《答徐懋庸并關(guān)于抗日統(tǒng)一戰(zhàn)線問題》,而后面發(fā)表的這兩篇文章,魯迅都已經(jīng)放進(jìn)了待編的《且介亭雜文末編》文稿里了,單單把在同一雜志上發(fā)表而且時(shí)間相距這么近的一篇回憶散文《我的第一個(gè)師父》剔開,顯然作者是另有考慮的。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不論他對于論戰(zhàn)性的雜文還抱有多大的熱情,有一個(gè)客觀的事實(shí)擺在了他眼前,即“左聯(lián)”已經(jīng)解散,甚至他認(rèn)為是潰散,這使得他不得不在寫作的重心上有所轉(zhuǎn)移,做出重新的選擇。當(dāng)時(shí)的大環(huán)境是,左翼文藝界領(lǐng)導(dǎo)者,正傾全力執(zhí)行化敵為友的國防文學(xué)政策,這對于一個(gè)堅(jiān)決的反對專制主義、反對獨(dú)裁政治的自由主義知識(shí)分子來說,無異于釜底抽薪,使之失去所攻擊的對象,失去了他那如匕首般的雜文的功能了。這比五四時(shí)期《新青年》團(tuán)體解散后成為了“游勇”還令人灰心,雖然那時(shí)本來就是自由結(jié)合的團(tuán)體消散了,朋友情誼都還是在的,最重要的是它允許“游勇”的存在。就說《新青年》同人,所謂左右分化之后,左派的陳獨(dú)秀與右翼的胡適仍然是朋友,而且可以說是非常牢靠的朋友。1923年底他們兩人應(yīng)邀為亞東圖書館老板汪孟鄒編輯的《科學(xué)與人生觀》一書各寫了一篇序言,這是他們兩人攜手共同批判唯心主義玄學(xué)、批判張君勱和梁啟超的世界觀的一次思想論戰(zhàn)。在協(xié)同作戰(zhàn)中,他們兩人之間也進(jìn)行了關(guān)于唯物論哲學(xué)的探討,其時(shí)二人之間的思想分歧是帶根本性的,政治理念也很不相同。胡適后來回憶說:“這部二十萬字的集子,我做了一篇序,陳先生也寫了一篇,他極力反駁我,質(zhì)問我,陳先生那時(shí)已轉(zhuǎn)到馬克思主義那方面去了。他問我所說馬克斯的唯物史觀可以解釋大多數(shù)的話,能否再進(jìn)一步,承認(rèn)它能解釋一切。……他是注重經(jīng)濟(jì)條件的,我也沒有反駁他,因?yàn)樗环裾J(rèn)人的努力,兩個(gè)人的主張不算沖突,不過客觀的條件雖然重要,但不僅限于經(jīng)濟(jì)一個(gè)條件,至于文化的條件,政治的條件,也是不能否認(rèn)的。”(《陳獨(dú)秀與文學(xué)革命——在北大國文系的講演》)陳獨(dú)秀確實(shí)是對胡適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他在所寫序言中說:“……適之最近對我說,‘唯物史觀至多只能解釋大部分的問題’,經(jīng)過這回辯論之后,適之必能百尺竿頭更進(jìn)一步!”(《陳獨(dú)秀先生序》,1923.11.13,轉(zhuǎn)引自《胡適文存二集·〈科學(xué)與人生觀〉序》)但胡適卻說:“……我個(gè)人至今還只能說:‘唯物(經(jīng)濟(jì))史觀至多只能解釋大部分的問題’。獨(dú)秀希望我‘百尺竿頭更進(jìn)一步’,可惜我不能進(jìn)這一步了。”(《胡適文存二集·〈科學(xué)與人生觀〉序》附錄二《答陳獨(dú)秀先生(適)》,1923.11.29)實(shí)際上他們之間圍繞序言中提出的哲學(xué)命題后來一來一往的質(zhì)疑、互答,反而超越了與原批判對象所進(jìn)行的討論,深化了這次思想論爭。此時(shí)的陳獨(dú)秀已是一個(gè)完全的政治人物,是中國共產(chǎn)黨的領(lǐng)袖了,他并沒有因此視胡適為代表資產(chǎn)階級(jí)利益的右翼反動(dòng)知識(shí)分子;而胡適卻依然是一個(gè)純?nèi)坏膶W(xué)者,他也沒有因?yàn)殛惇?dú)秀信仰馬克思主義而視其為政治危險(xiǎn)人物,盡管在《新青年》時(shí)期他是反對“赤化”的。他們在哲學(xué)上甚至政治思想上,能夠求同存異,沒有勢不兩立;他們兩人都能夠做到如此的寬容,達(dá)到這樣的境界,原因在于他們都具有高度的民主意識(shí)和科學(xué)的頭腦,畢竟他們二位是中國近代高舉“德先生”和“賽先生”的旗手。
這里我們可以再看一個(gè)事實(shí)。十年之后,1932年10月,陳獨(dú)秀在上海租界被捕,后關(guān)押南京。此次被捕非同十幾年前國民黨尚未當(dāng)政之時(shí)的前幾次被捕可比,此時(shí)共產(chǎn)黨已處于匪徒的地位,而陳獨(dú)秀被視為赤匪之巨魁。起初國民黨是要按軍事法庭特別審判的,后迫于朝野的強(qiáng)大壓力——當(dāng)時(shí)蔡元培、胡適、翁文灝、傅斯年、章士釗等都進(jìn)行了營救,國民黨當(dāng)局只得放棄秘密審判。1932年10月22日致電翁文灝并轉(zhuǎn)胡適等,特別告訴他們:“陳獨(dú)秀案已電京移交法院公開審判矣。”(《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冊,中華書局1979年版)這樣就使得當(dāng)局不能秘密對陳獨(dú)秀下毒手了,至少不會(huì)像一年多前在上海龍華警備司令部被秘密殺害的二十多位烈士那樣,無聲無息的離開了人間。
陳氏非常清楚這次坐牢一時(shí)是難脫羈絆的了,他甚至做好了“大辟”的準(zhǔn)備。此時(shí)他本能的恢復(fù)了學(xué)者的原貌,他把監(jiān)獄當(dāng)作研究室,竟然繼續(xù)從事他的社會(huì)科學(xué)研究工作了。他在獄中寫信給胡適,開了書單:
英文《原富》,亞當(dāng)斯密的
英文李嘉圖的《經(jīng)濟(jì)學(xué)與賦稅之原理》
英文馬可波羅的《東方游記》
崔適先生的《〈史記〉探源》
此外,關(guān)于甲骨文的著作,也希望能找?guī)追N寄給我……
存尊處的拼音文字稿,我想現(xiàn)在商務(wù)可以放心出版了,倘商務(wù)還不敢出版,能改由孟真先生在研究所出版否?弟頗欲此書能早日出版,能引起國人批評(píng)和注意①。
這真正是一貫徹底的實(shí)行了自己的信念,他說:“世界文明發(fā)源地有二:一是科學(xué)研究室,一是監(jiān)獄。我們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監(jiān)獄,出了監(jiān)獄就入研究室。這才是人生最高尚優(yōu)美的生活。從這兩處發(fā)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價(jià)值的文明。”(《研究室與監(jiān)獄》,1919年6月8日《每周評(píng)論》第25號(hào))由此可見陳獨(dú)秀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政治家兼學(xué)者而非政客加流氓。
這之后陳獨(dú)秀還請胡適物色可靠的翻譯家組織翻譯《資本論》。胡適回信說:
仲兄:
手示敬悉。
《資本論》,此間已托社會(huì)調(diào)查所吳半農(nóng)、千家駒兩君合譯,已脫稿的第一冊有三分之二了。第一分冊已在四月前付商務(wù)排印。此二人皆極可靠,皆能用英德兩國本子對勘。……②
此事在陳獨(dú)秀說來,這種直接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工作,如果不是極可信任、極為博學(xué)的朋友是可以輕易就委托他去做的嗎?就像當(dāng)年他向蔡元培推薦胡適到北大做教授時(shí)一樣的信任,這里絲毫沒有什么“左翼”或“右翼”一類的顧忌;而對于胡適來說,這種極不合時(shí)宜的、具有相當(dāng)風(fēng)險(xiǎn)的文化傳播工作,如果不是自己對于西方政治經(jīng)濟(jì)學(xué)有相當(dāng)?shù)恼J(rèn)識(shí),如果不是對于委托人懷有十分的敬意,并且不是一位交誼甚深的非常具有才學(xué)的政治活動(dòng)家朋友的委托是可以隨便就接受承應(yīng)下來的嗎?何況此時(shí)陳獨(dú)秀已陷囹圄,勢利膽小之人應(yīng)該是避之而唯恐不及的。
陳獨(dú)秀在獄中除了讀書從事研究之外,而且在法庭上與當(dāng)局進(jìn)行了堅(jiān)決的斗爭。在庭審時(shí)他宣稱中國托派(中國共產(chǎn)黨左派反對派)的最終目的是:“世界革命,在中國需要解放民眾,提高勞動(dòng)者生活。關(guān)于奪取政權(quán),乃當(dāng)然的目的。”(《陳獨(dú)秀被捕資料匯編·陳獨(dú)秀開審記》,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轉(zhuǎn)引自王觀泉著《“天火”在中國燃燒》,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05年版)他在《辯訴狀》中寫道:“半殖民地的中國,經(jīng)濟(jì)落后的中國,外困于國際帝國資本主義,內(nèi)困于軍閥官僚。欲求民族解放,民主政治之成功……只有最受壓迫最革命的工農(nóng)勞苦人民和全世界反帝國主義反軍閥官僚的無產(chǎn)階級(jí)勢力,聯(lián)合一起,以革命怒潮,對外排除帝國主義的宰割,對內(nèi)掃蕩軍閥官僚的壓迫,……”這完全不是在為自己辯護(hù),而是利用合法權(quán)利毫不畏懼的在敵人的法庭上傳播馬克思主義,宣傳反帝反封建的共產(chǎn)主義者的主張了。1933年4月,他以共產(chǎn)黨要犯身份,以文字作叛國宣傳等罪名被判處了八年徒刑。雖然他沒有為自己爭得自由,但是作為一個(gè)革命家,他竟在失去自由的情況下,利用敵人的法庭打了一個(gè)漂亮的勝戰(zhàn):他將這次審判文件編成一本《陳案書狀匯錄》交老友汪孟鄒的亞東圖書館私下出版。這本非法圖書,收錄有:《檢察官起訴書》、《陳獨(dú)秀自撰辯訴狀》、《章士釗律師辯護(hù)詞》、《南京中央日報(bào)論文》、《章士釗答中央日報(bào)》、《江蘇高院判決書》等案卷材料及文章,當(dāng)時(shí)是具有轟動(dòng)效應(yīng)的,甚至上海一些大學(xué)法學(xué)系將此作為教材的案例。雖然中國的托派的對敵斗爭已經(jīng)被摒棄于中國共產(chǎn)黨政治斗爭史之外,思想文化領(lǐng)域里的抗?fàn)幰膊粚儆谧笠砦膶W(xué)運(yùn)動(dòng)之范疇,但遍觀左翼文學(xué)運(yùn)動(dòng)史,能與《陳案書狀匯錄》一樣的與國民黨統(tǒng)治集團(tuán)進(jìn)行這么尖銳的正面斗爭的具有歷史意義的革命文獻(xiàn)實(shí)在是少見。當(dāng)代中共黨史研究家對于陳獨(dú)秀審判案卷匯編的評(píng)價(jià)是:它與1848年《新萊茵報(bào)》事件中馬克思所撰的《揭露科倫共產(chǎn)黨人案》,與1933年“國會(huì)縱火案”中季米特洛夫在萊比錫法庭上抗辯的《控訴法西斯》一樣,均是利用敵人的法庭傳播共產(chǎn)主義思想的經(jīng)典文獻(xiàn)。(參閱《天火在中國燃燒·陳獨(dú)秀的國勢調(diào)查與新文化運(yùn)動(dòng)》)
《新青年》左右翼分化之后,魯迅與陳獨(dú)秀同樣也仍然保持著良好的朋友關(guān)系。魯迅一直很感念陳獨(dú)秀動(dòng)員他寫小說之事,他完全明白,沒有《新青年》和陳獨(dú)秀就沒有中國現(xiàn)代小說開山祖之譽(yù)的魯迅,所以他后來在《我怎么做起小說來》(1933.3.5)這篇文章中就明明白白記下了這一筆:“但是《新青年》的編輯者,卻一回一回的來催,催幾回,我就做一篇,這里我必得記念陳獨(dú)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說最著力的一個(gè)。”現(xiàn)在我們還能看到陳獨(dú)秀寫給周作人信中的這樣的話:“我們很盼望豫才先生為《新青年》創(chuàng)作小說,請先生轉(zhuǎn)告他。”(1920.3.11)“魯迅兄做的小說,我實(shí)在五體投地的佩服。”(1920.8.22)陳獨(dú)秀的催稿信現(xiàn)在已是魯迅研究的珍貴資料。1933年魯迅記下對陳獨(dú)秀表示感激的這一筆的時(shí)候,也正是陳獨(dú)秀身陷囹圄之時(shí),并且早已遭到共產(chǎn)國際的嫁禍和清算,被中共開除出黨了;而此時(shí)魯迅卻是中共外圍組織“左聯(lián)”中人,并被視為左翼文學(xué)的旗幟了。由此可見,魯迅是珍重歷史的,他并未受“左聯(lián)”中共產(chǎn)黨人的成見的影響。
至于魯迅與胡適,當(dāng)時(shí)他們更是學(xué)術(shù)上能夠切磋的好友。《新青年》的分化,一般以胡適1920年12月間寫給陳獨(dú)秀的“發(fā)難”信作為分化的標(biāo)志。當(dāng)時(shí)胡適和北京的同人們看到《新青年》越來越政治化,已經(jīng)直接介于政治斗爭,這已經(jīng)超出了文藝復(fù)興性質(zhì)的文學(xué)革命、思想啟蒙主義的奮斗宗旨;而此時(shí)《新青年》的出版發(fā)行又受到大的壓迫,已經(jīng)被當(dāng)局禁止郵寄發(fā)行,出于挽救這份具有歷史意義的雜志的考慮,胡適便寫出這封回答陳獨(dú)秀并上海編輯部的信。在這封信中胡適提出了三條意見供陳獨(dú)秀考慮:
1.聽《新青年》流為一種有特別色彩之雜志,而另創(chuàng)一個(gè)哲學(xué)文學(xué)的雜志,……
2.若要《新青年》“改變內(nèi)容”,非恢復(fù)我們“不談?wù)巍钡慕浼s,不能做到。但此時(shí)上海同人似不便做此一著,兄似更不便,因?yàn)椴辉甘救艘匀酢5本┩苏环寥绱诵浴9饰抑鲝埑眯蛛x滬的機(jī)會(huì),將《新青年》編輯部的事,自九卷一號(hào)移到北京來。由北京同人于九卷一號(hào)內(nèi)發(fā)表一個(gè)新宣言,略根據(jù)七卷一號(hào)的宣言,而注重學(xué)術(shù)思想藝文的改造,聲明不談?wù)巍?/p>
3.孟和說,《新青年》既被郵局停寄,何不暫時(shí)停辦,此是第三辦法。但此法與“新青年社”的營業(yè)似有妨礙,故不如前兩法。③
胡適這封信的三條意見,簡單地說,就是:一,分家。即上海的《新青年》任其政治化,北京另辦一個(gè)純學(xué)術(shù)的雜志。二,遷移。即《新青年》編輯部移回北京,并發(fā)表宣言重申不談?wù)巍⒆⒅貙W(xué)術(shù)和文藝的辦刊宗旨。三,停刊。即在目前難以為繼的情況下索性就此關(guān)閉。
這之前陳獨(dú)秀的來信是寫給北京全體同人的,大家都先后傳閱了。胡適的這封回信也向在京的朋友們征求了意見,大家也都各抒了己見,可以說胡適是代表北京的同人回答陳獨(dú)秀的。事實(shí)上北京的同人基本上都贊同胡適的意見,即贊成胡適信中所提的前兩條方案,包括左翼代表人物。胡適告訴陳獨(dú)秀:“此信一涵、慰慈見過。守常、孟和、玄同三人知道此信的內(nèi)容。他們對于前兩條辦法,都贊成,以為都可行。馀人我明天通知。”魯迅接到胡適的通知后,態(tài)度十分明確:“我的意思是以為三個(gè)都可以的,但如北京同人一定要辦,便可以用上兩法而第二個(gè)辦法更為順當(dāng)。”并且他還代表周作人答復(fù),同意采取第二種辦法。雖然他在信中表示不同意聲明不談?wù)危囊馑际沁@種宣言、聲明無用、多余,而不是從原則上反對“恢復(fù)我們‘不談?wù)巍慕浼s”。他以為“此后只要學(xué)術(shù)思想藝文的氣息濃厚起來——我所知道的幾個(gè)讀者,極希望《新青年》如此,就好了。”(《魯迅全集》第11卷《210103致胡適》,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81、2005年版)這表明他更注重實(shí)際,不事張揚(yáng),只要切實(shí)的去做,堅(jiān)持注重學(xué)術(shù)和文藝的辦刊方向“就好了”。
胡適代表北京同人的表態(tài),使陳獨(dú)秀大為光火,他寫信指責(zé)胡適拆臺(tái)是反對《新青年》、反對他本人。為消除誤會(huì),胡適立即收回了第一條和第三條辦法,并且也收回了第二條中特別提出的聲明“不談?wù)巍钡慕ㄗh,僅保留了《新青年》遷回北京來編輯這一點(diǎn),并再次寫信請北京同人進(jìn)行表決。表決的結(jié)果與第一次基本一樣,在原則上沒有什么改變,這里只引三位最具代表性的意見:
1.:“我還是主張從前的第一條辦法。但如果不致‘破壞《新青年》精神之團(tuán)結(jié)’,我對于改歸北京編輯之議亦不反對,而絕對的不贊成停辦,因停辦比分裂還不好。”
胡適在的意見之下有一條注:“后來守常也取消此議,改主移京編輯之說。”
還特別另寫了一信給胡適,約胡適當(dāng)面細(xì)談,因?yàn)殛惇?dú)秀信中還委婉的批評(píng)了胡適等政治傾向上的問題:“南方頗傳適之兄與孟和兄與研究系接近,且有惡評(píng)……我盼望諸君宜注意此事”(1920.12.16陳獨(dú)秀致胡適、高一涵信),同意錢玄同的意見:“……關(guān)于研究系謠言問題,我們要共同給仲甫寫一信,去辯明此事。”(1921年1月致胡適信)胡適在的表決意見之下批注的“后來守常也取消此議,改主移京編輯之說”,當(dāng)是他們面談之后的結(jié)果。
2.周作人:“贊成北京編輯。但我看現(xiàn)在《新青年》的趨勢是傾于分裂的,不容易勉強(qiáng)調(diào)和統(tǒng)一。無論用第
一、第二條辦法,結(jié)果還是一樣,所以索性任他分裂,照第一條做或者倒還好一點(diǎn)。”
3.周作人是代表他們弟兄兩人寫的意見的,但魯迅在周作人寫的意見之下又補(bǔ)充了一句:“與上條一樣,但不必爭《新青年》這一個(gè)名目。”④
北京同人的表決都是直接寫在胡適的信上的,所以這些珍貴的歷史文獻(xiàn)資料也隨著胡適的書信保留了下來。
這次表決只有一個(gè)變化,就是由原來大家比較贊成的魯迅所說“最為順當(dāng)”的第二條,現(xiàn)在基本上都贊成第一條另起爐灶的方案了。可見北京同人們的態(tài)度是非常一致的,也非常的堅(jiān)定。
這就是《新青年》分化的真面目。如果要分左右兩翼,、魯迅均屬于胡適的右翼,并非過去一般所說魯迅的態(tài)度與胡適針鋒相對。當(dāng)時(shí)上海編輯部與北京《新青年》同人處于一種對立的態(tài)勢倒是比較近于事實(shí)的。陳獨(dú)秀將《新青年》不自覺的視為其私產(chǎn),或視為其政黨組織的思想文化宣傳的陣地,而對于昔日的同人們沒有表現(xiàn)出足夠的尊重,在事先沒有征得同人們的同意下就把《新青年》交給他在上海的同志陳望道、沈雁冰等人去辦了,事后僅僅寫信打一個(gè)招呼,而且還是因?yàn)楦逶磫栴},需向北京的朋友們催稿才告知的,他希望北京的朋友繼續(xù)支持《新青年》,準(zhǔn)確的說是繼續(xù)支持由他所委托的人主持的《新青年》。陳獨(dú)秀很清楚,《新青年》的優(yōu)秀作者隊(duì)伍當(dāng)時(shí)都集中在北京;但是北京的同人們一致要求《新青年》移回北京辦,這實(shí)際上就是對于上海編輯部表示抵制。陶孟和則以當(dāng)局禁止郵寄《新青年》雜志為理由,建議索性停刊(即胡適信中提出的第三條意見,這一條魯迅也并不反對);錢玄同則顯得很沖動(dòng),他說:
與其彼此隱忍遷就的合并,還是分裂的好。要是移到北京來,大家感動(dòng)[情]都不傷,自然可移;要是比分裂更傷,還是不移而另辦為宜。……《新青年》若全體變?yōu)椤短K維埃俄羅斯》的漢譯本,甚至于說這是陳獨(dú)秀、陳望道、李漢俊、袁振英等幾個(gè)人的私產(chǎn),我們也只可說陳獨(dú)秀等辦了一個(gè)“勞農(nóng)化”的雜志,叫做《新青年》,我們和他全不相干而已,斷斷不能要求他們停板。⑤
錢玄同主張《新青年》要么移京,要么各辦各的,而且非常明顯的流露了對于上海編輯部的不滿情緒。如果一定要將五四《新青年》團(tuán)體分為左右兩翼的話,左翼就是:以上海陳獨(dú)秀為首的政黨報(bào)刊派,包括后起之秀陳望道、沈雁冰等人;右翼就是:以北京胡適為首的學(xué)術(shù)藝文派,包括、魯迅、周作人、錢玄同等人。最后陳獨(dú)秀堅(jiān)決拒絕了北京同人的建議,他給胡適回信說:“我當(dāng)時(shí)不贊成《新青年》移北京,老實(shí)說是因?yàn)榻鼇泶髮W(xué)空氣不大好,現(xiàn)在《新青年》已被封禁,非移粵不能出版,移京已不成問題了。你們另外辦一個(gè)報(bào),我十分贊成,因?yàn)橹袊脠?bào)太少,你們做出來的東西總不差,但我卻沒有工夫幫助文章。而且在北京出版,我也不宜做文章。”(1921年2月15日陳獨(dú)秀致胡適信,編入《中國出版史料(現(xiàn)代部分)》第一卷上冊)這樣雙方都同意分手了。以后的結(jié)果正如錢玄同所說,《新青年》終于成為了《蘇維埃俄羅斯》的漢譯本,并且成為了中共機(jī)關(guān)刊物,這當(dāng)然與北京的朋友們就全不相干了。從學(xué)術(shù)的角度抑或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后期的《新青年》,尤其是完全成為中國共產(chǎn)黨機(jī)關(guān)刊之后由瞿秋白主編的《新青年》季刊和不定期刊(1923.6~1926.7)與五四時(shí)代的《新青年》的確不能再視為同一刊物了,因?yàn)樗呀?jīng)完全屬于一個(gè)政黨的機(jī)關(guān)報(bào)刊,而非一群信仰民主科學(xué)的自由主義知識(shí)分子自由結(jié)合的同人刊物,只是它保留了其前身的英名而已。
在五四新文化運(yùn)動(dòng)時(shí)期,尤其魯迅在八道灣居住時(shí)期,胡適與周氏兄弟在《新青年》未來走向上意見一致,同屬于學(xué)術(shù)藝文派,相處甚為融洽。他們時(shí)相往來,討論文學(xué)創(chuàng)作,如為胡適《嘗試集》再版修訂提刪改意見。胡適對他們也極為尊重:“我所知道的‘新詩人’,除了會(huì)稽周氏兄弟之外,大都是從舊式詩、詞、曲里脫胎出來的。”(《談新詩》,《胡適文存》卷一)在古典小說研究上他們更是互相切磋,如關(guān)于《西游記》故事源流及作者的考證,《水滸》古版本的整理研究等,現(xiàn)在還保留有他們這方面交往的通信。這一時(shí)期胡適日記里也可以反映出他們之間的友好交往,如1922年3月4日他去八道灣周宅:“與啟明、豫才談翻譯問題。豫才深感現(xiàn)在創(chuàng)作文學(xué)的人太少,勸我多作文學(xué)。我沒有文學(xué)的野心,只有偶然的文學(xué)沖動(dòng)。”(《胡適的日記》上冊,中華書局1985年版)1922年8月11日他去周氏兄弟家聊天,這天的日記寫道:“講演后,去看啟明,久談,在他家吃飯;飯后,豫才回來,又久談。周氏弟兄最可愛,他們的天才都很高。豫才兼有賞鑒力與創(chuàng)造力,而啟明的賞鑒力雖佳,創(chuàng)作較少。”(《胡適的日記》下冊)1923年12月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講義稿上冊出版,分贈(zèng)給同人。胡適、錢玄同等均認(rèn)真的閱讀了并提出了意見。對這些意見魯迅十分重視,他立即回信給胡適說:“今日到大學(xué)去,收到手教。《小說史略》(頗有誤字,擬于下卷附表訂正。)竟承通讀一遍,慚愧之至。論斷太少,誠如所言,玄同說亦如此。我自省太易流于感情之論,所以力避此事,其實(shí)正是一個(gè)缺點(diǎn),但于明清小說,則論斷似較上卷稍多,此稿已成,極想于陽歷二月末印成之。”(1923年12月28日)魯迅胡適之間的這些友好交往,已經(jīng)早就離開《新青年》的時(shí)代了。
魯迅與胡適的疏離是在與現(xiàn)代評(píng)論派論爭之后,但胡適并未卷入這場論爭,而是保持中立。即使是后來他們的政見不同,二人始終也未成為論敵,更未成為仇敵。魯迅談到他對劉半農(nóng)的感情時(shí)說:“我愛十年前的半農(nóng),而憎惡他的近幾年。這憎惡是朋友的憎惡,……”(《憶劉半農(nóng)君》,1934)對于胡適,魯迅卻一直是很敬佩的,還談不到“憎惡”,至多是因政見分歧而生反感,但也應(yīng)該是“朋友的反感”,敬而遠(yuǎn)之,最多譏諷幾句而已;早在《新青年》時(shí)期,他就說過他很佩服陳胡,卻對于他們敬而遠(yuǎn)之這種意思的話。應(yīng)該看到,直到三十年代,魯迅胡適還曾同屬于中國民權(quán)保障同盟的同志,直到胡適與同盟的上海中央領(lǐng)導(dǎo)人鬧翻后為止。魯迅逝世后,胡適還同意參加魯迅紀(jì)念委員會(huì),并為《魯迅全集》的出版出力。
對于《新青年》團(tuán)體的散掉,魯迅雖然感到失望,感到寂寞,像在“沙漠中走來走去”,但是他始終是抱著惋惜與懷念的感情的,他后來稱那個(gè)時(shí)期的作品為“吶喊”,為“遵命文學(xué)”,他所遵奉的“是那時(shí)革命的前驅(qū)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自選集〉自序》,1932)。這里說的“革命的前驅(qū)者”,就是指的陳獨(dú)秀和胡適等新文化運(yùn)動(dòng)的領(lǐng)袖們、同人們。
但是到了左翼文學(xué)運(yùn)動(dòng)時(shí)期(1927—1936),從一開始,魯迅就與他本來十分愿意合作的人們相處得很不愉快。1926年魯迅還在廈門大學(xué)時(shí),就已經(jīng)有了到廣州后“與創(chuàng)造社聯(lián)合起來,造一條戰(zhàn)線,更向舊社會(huì)進(jìn)攻”的想法(見《兩地書》第二集第六十九信);創(chuàng)造社也愿意與魯迅聯(lián)合辦刊物。1927年底魯迅已列名為擬復(fù)刊的《創(chuàng)造周報(bào)》的特約撰稿人,1928年1月《創(chuàng)造月刊》刊登的《創(chuàng)造周報(bào)復(fù)活了》的預(yù)告上魯迅還列名為編輯委員。可是他們僅僅達(dá)成了一個(gè)協(xié)議,還沒有進(jìn)行一次合作,創(chuàng)造社的“革命作家”們就變卦了,不僅是變卦,撕毀了已向世人刊布的預(yù)告,而且反目為仇,他們宣布魯迅是“資本主義以前的一個(gè)封建余孽”,“資本主義對于社會(huì)主義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對于社會(huì)主義是二重的反革命”,因此,“魯迅是二重的反革命的人物”,“他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諦)!”(見杜荃即郭沫若文章《文藝戰(zhàn)線上的封建余孽——批評(píng)魯迅的〈我的態(tài)度氣量和年紀(jì)〉》,發(fā)表于1928.8.10《創(chuàng)造月刊》第2卷第1期)這樣的定性,比后來國民黨浙江省黨部的頭目許紹棣稱魯迅為“墮落文人”簡直還要罪加十等,毫無疑問魯迅就成了首先應(yīng)該被革掉命的人,所以遭到這一批不可一世的“革命文學(xué)”者們的極其猛烈的圍攻,如同“假洋鬼子”不許阿Q革命一樣,竟給予了阿Q的作者和他的主人公同等的待遇。當(dāng)時(shí)的左派們對于魯迅的否定是徹底的,連新文化運(yùn)動(dòng)時(shí)期的小說創(chuàng)作也被他們說得幾乎一文不值,認(rèn)為多是庸俗淺薄的作品。幸好這些“革命作家”當(dāng)時(shí)尚未取得“幫忙與幫閑”的地位,僅止于口誅筆伐而已。
創(chuàng)造社、太陽社等激進(jìn)派對魯迅的圍攻后來經(jīng)中共中央宣傳部及時(shí)制止糾正,并經(jīng)調(diào)解雙方實(shí)現(xiàn)了大聯(lián)合,于1930年初成立了統(tǒng)一戰(zhàn)線性質(zhì)的“中國左翼作家聯(lián)盟”組織。魯迅也早愿從沙漠中走出,加入到新的陣營中來。他在彷徨之中曾自問:“新的戰(zhàn)友在那里呢?”(《自選集》自序)毫無疑問“左聯(lián)”同志就是他找到的新的戰(zhàn)友了。當(dāng)時(shí)魯迅還是抱著一種十分友善的態(tài)度,認(rèn)為創(chuàng)造社對他的批評(píng)促進(jìn)了他對于馬克思文藝?yán)碚摰奈眨⒈剖顾g了幾本馬克思主義文藝?yán)碚撝鳎@是他要表示感激的。不過從他在左翼作家聯(lián)盟成立大會(huì)的講話上來看,他是并沒有完全失掉戒心的。他的講話一開頭就引起昔日論敵的不滿,他說:“我以為在現(xiàn)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為‘右翼’作家的。為什么呢?第一,倘若不和實(shí)際的社會(huì)斗爭接觸,單關(guān)在玻璃窗內(nèi)做文章,研究問題,那是無論怎樣的激烈,‘左’,都是容易辦到的;然而一碰到實(shí)際,便即刻要撞碎了。關(guān)在房子里,最容易高談徹底的主義,然而也最容易‘右傾’。”(《對于左翼作家聯(lián)盟的意見》,1930.3)這篇講話幾乎通篇是針對左翼宗派主義者的,也非常切中要害。他提醒他的新盟友們:不要“反而弄成了在一角里新文學(xué)者和新文學(xué)者的斗爭,舊派的人倒能夠閑舒地在旁邊觀戰(zhàn)。”然而,他竟不幸而言中了,后來的事實(shí)說明,雙方一直相處得不融洽,以致再次發(fā)生論爭,最終決裂。魯迅與上海地下黨左翼文學(xué)領(lǐng)導(dǎo)人的貌合神離的關(guān)系維持到1936年初“左聯(lián)”解散。在魯迅去世前發(fā)生了“國防文學(xué)”與“大眾文學(xué)”的論爭,到此時(shí)魯迅內(nèi)心里已經(jīng)把從背后射暗箭的屬于同一營壘里的所謂戰(zhàn)友視為了敵人,而且對于他們的憎惡是在他的正面的敵人(統(tǒng)治階級(jí))之上的,他不能再像“左聯(lián)”成立之前“革命文學(xué)”論爭時(shí)那樣的寬容了。這不是他的心胸褊狹,而是幾年來同一陣營里的“奴隸主”及“工頭們”給予他的教訓(xùn)使他獲得的最新的認(rèn)識(shí)。這一認(rèn)識(shí)給他的觸動(dòng),并不低于1927年的恐怖對于他的震動(dòng)。盡管他呼吸的最后一刻還在與對手爭論“國防文學(xué)”與“大眾文學(xué)”,其實(shí)他心中已經(jīng)完全清楚,正面的敵營已經(jīng)消除,至少在意識(shí)上強(qiáng)行取消了,一切有形的敵人都已化為或即將化為無形之?dāng)沉恕Kf:“‘聯(lián)合戰(zhàn)線’之說一出,先前投敵的一批‘革命作家’,就以‘聯(lián)合’的先覺者自居,漸漸出現(xiàn)了。納款,通敵的鬼蜮行為,一到現(xiàn)在,就好像都是‘前進(jìn)’的光明事業(yè)。”(《半夏小集》,1936年)如果這一幫鬼蜮們只是對自己的鬼蜮行徑負(fù)責(zé),并不壓迫他人也就罷了,可是由于魯迅拒絕參加他們組織的中國文藝家協(xié)會(huì),不愿被人當(dāng)作傀儡,竟被指責(zé)是破壞抗日統(tǒng)一戰(zhàn)線。1936年7月17日他在寫給瞿秋白夫人楊之華的信中說:“當(dāng)病發(fā)時(shí),新英雄們正要用偉大的旗子,殺我祭旗,然而沒有辦妥,愈令我看穿了許多人的本相。”(見《魯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6期)在當(dāng)時(shí),假如他還留念戰(zhàn)場,竟想獨(dú)戰(zhàn),就有宣布為“托派”和漢奸的危險(xiǎn),實(shí)際上也早已有這樣的謠言了,所以他在重病之中由他的密友馮雪峰主動(dòng)為他寫了一篇《答托洛斯基派的信》(1936.6.9)公開發(fā)表了。此文猶如一個(gè)黨外布爾什維克的表態(tài),并不像是作為一個(gè)反政府的左翼作家的態(tài)度。值得注意的是,這篇引人注目的文章和另一篇由馮的文章《論現(xiàn)在我們的文學(xué)運(yùn)動(dòng)》(1936.6.10),魯迅后來都沒有同《答徐懋庸并關(guān)于抗日統(tǒng)一戰(zhàn)線問題》(1936.8)一樣放到待編的這年的雜文集里,顯然這是有意不收入的。當(dāng)時(shí)他的內(nèi)心是很矛盾的,一方面他對于謠言極為氣憤,另一方面他也不愿意為了洗涮表白自己而去攻訐、傷害一個(gè)他一直懷有敬意此刻還坐在國民黨牢中的老友;對于異國的革命家托洛茨基,他也認(rèn)為是一位具有很高文藝修養(yǎng)的革命家,他本人的一些文藝思想就有來源于他的,這種情結(jié)恐怕也難以頃刻就完全丟棄不顧的。胡風(fēng)晚年關(guān)于馮雪峰為魯迅撰寫此文的回憶,透露了魯迅的這種心情,并披露了一個(gè)重要情況:一,《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及《論現(xiàn)在我們的文學(xué)運(yùn)動(dòng)》并非魯迅委托馮雪峰所寫,當(dāng)時(shí)魯迅臥病在床,連話都不能說,更無法仔細(xì)思考問題了;二,魯迅身體稍恢復(fù)之后,明確表示了對文章不滿意的意思,說一點(diǎn)也不像他的東西。胡風(fēng)說:“魯迅在思想問題上是非常嚴(yán)正的,要他對沒有經(jīng)過深思熟慮(這時(shí)候決不可能深思熟慮)的思想觀點(diǎn)擔(dān)負(fù)責(zé)任,那一定要引起他精神上的不安,……”(《魯迅先生》,1984。載《新文學(xué)史料》1993年第1期)這一情形很引起了中國托派元老們的關(guān)注、重視。鄭超麟先生就寫了《讀胡風(fēng)〈魯迅先生〉長文有感》,發(fā)表在《魯迅研究月刊》上;還有王凡西、樓子春等在海外發(fā)表了文章,對于這種情況表示理解,同時(shí)也恢復(fù)對魯迅的尊敬。鄭超麟說:“由此可見,在馮雪峰代擬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中,用辱罵代替戰(zhàn)斗,用‘日圓說’代替‘盧布說’,這二方面,魯迅本人實(shí)在不能負(fù)責(zé)。”(載《魯迅研究月刊》1993年第10期)事實(shí)也是如此,同樣是馮雪峰,但是經(jīng)過魯迅深思熟慮、精心修改的《答徐懋庸并關(guān)于抗日統(tǒng)一戰(zhàn)線問題》就放到《且介亭雜文末編》里了,而攻訐托派的文章他是沒有認(rèn)可的,所以他自己并沒有收入;現(xiàn)在我們看到的是后來的編者作為附錄收入的。1957年打右派批判馮雪峰時(shí),為了掩飾“左聯(lián)”中的問題,當(dāng)時(shí)的說法是《答徐懋庸》系馮雪峰所擬稿,它并不符合魯迅的原意;現(xiàn)在人們已經(jīng)可以看到《魯迅手稿全集》中此篇的原稿,上面有魯迅大量修改的筆跡,今天誰也不懷疑這是魯迅的作品了。倒是《答托洛斯基派的信》這篇文章,這實(shí)在是馮雪峰擔(dān)憂過度,他既為魯迅卻未能珍重魯迅的為人,也未能夠把握好魯迅的思想和文風(fēng),更不可取的是他把魯迅當(dāng)作黨的馴服工具來使用,還覺得魯迅沒有像高爾基那樣聽黨的話(參閱胡風(fēng)《魯迅先生》)。《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表面上是答復(fù)托派的,實(shí)質(zhì)是為了急于向左翼文學(xué)陣營中的謠言制造者表示自己與托派“漢奸”毫無干系,不但無干系,而且特別表白了自己擁護(hù)斯大林的蘇聯(lián),擁護(hù)陜北蘇區(qū)的中共中央的心愿。托派的這封信只是一封個(gè)人的私信,而且其中對于時(shí)局的觀點(diǎn)也并非都與魯迅思想相左,如對于國民黨的態(tài)度,按理對此信是沒有理由必須公開表態(tài)予以譴責(zé)的。1972年12月25日魯迅博物館開了一個(gè)座談會(huì),此時(shí)正當(dāng)“”中,五十年代不能說的一些話此時(shí)卻可以說了,馮雪峰說:“不過魯迅先生的回信發(fā)表,對托派的打擊是相當(dāng)大的。一方面也回?fù)袅酥軗P(yáng)等人,所以《光明》半月刊和《文學(xué)界》都不肯發(fā)表,不但怕刊物被查封,也因其中回?fù)袅酥軗P(yáng)等人的緣故。”(胡愈之、馮雪峰:《談?dòng)嘘P(guān)魯迅的一些事情》,載《魯迅研究資料》第1輯,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直到三十六年之后,馮雪峰才透出了一點(diǎn)寫此信的真實(shí)意圖。答托派的這封公開信后來為王明、康生之流鉆了空子,他們大肆鼓噪羅織罪證,一口咬定陳獨(dú)秀是漢奸,但這與周揚(yáng)等已毫無關(guān)系了。王明是徹底的執(zhí)行莫斯科肅清世界各國托派的指示的。1937年12月王明、康生等從莫斯科飛抵延安,在隨即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huì)議上附帶討論了與陳獨(dú)秀恢復(fù)關(guān)系的問題。回憶說:當(dāng)時(shí)中央大部分人包括對陳獨(dú)秀都抱有若干同情,但是王明聲色俱厲的表示:“我們和甚么人都可以合作抗日,只有托派是例外。在國際上我們可以和資產(chǎn)階級(jí)的政客軍閥甚至反共劊子手合作,但不能與托洛斯基的信徒們合作。在中國我們可以與及其屬下的反共特務(wù)等等人合作,但不能與陳獨(dú)秀合作。”“斯大林正在雷厲風(fēng)行的反托派,而我們卻要聯(lián)絡(luò)托派,那還了得;如果斯大林知道了,后果是不堪設(shè)想的。”“反對托派,不能有仁慈觀念,陳獨(dú)秀即使不是日本間諜也應(yīng)說成是日本間諜。”(:《我的回憶》下冊,東方出版社2004年版)當(dāng)時(shí)王明一是以欽差身份發(fā)指令,同時(shí)他自己也恐懼陳獨(dú)秀可能卷土重來,東山再起,因此不遺余力的下此毒手。陳獨(dú)秀出獄后雖然主張拋開政見分歧和黨派成見,共同抗日,但此時(shí)他也已抱定“不擁國,不”的獨(dú)立態(tài)度了,毫無“歸隊(duì)”的意愿。盡管陳獨(dú)秀遭到王明、康生的誣陷,有一個(gè)最基本的事實(shí)是不能抹殺的:《答托斯基派的信》發(fā)表時(shí),陳獨(dú)秀的八年刑期尚未滿,仍被關(guān)在國民黨的監(jiān)獄里服刑,此時(shí)即使他要投敵也是絕對不可能的。直到抗戰(zhàn)全面爆發(fā)后,于1937年8月南京淪陷前夕他才減刑獲釋。日本侵華初期,日本侵略者以為可以一口吃掉中國,根本沒有把國民黨政權(quán)放在眼里,他們不把看作談判的對手,只允許他無條件投降,做亡國奴,不許議和,也就是不給與做漢奸的機(jī)會(huì)。這里我們可以看看當(dāng)時(shí)任國民黨宣傳部代部長,后來成為了真正漢奸的周佛海當(dāng)年想要做漢奸而尋不到門徑時(shí)的焦急如焚的心情,就可以知道日本人挑選漢奸并不是很隨意的。《周佛海日記》1937年9月1日寫道:“據(jù)云:蔣先生已完全同意原則(按:指派特務(wù)與日本聯(lián)系交涉外交解決途徑),惟恐事機(jī)不密,反多糾紛,且日人決不肯為吾輩守秘密也。但亦非全不進(jìn)行,須另設(shè)他法。稍為心慰。”一年后,交涉毫無進(jìn)展,1938年7月7日周佛海在日記中記道:“閱近衛(wèi)談話,不僅不以蔣政權(quán)為對象,且不以國民政府為對象;即使蔣氏下野,親日政治家出主政權(quán),亦不與國民政府交涉。是則一線和平之望亦已斷絕矣。”(中國社會(huì)科學(xué)出版社1986年版)后來的歷史果然是脫離了蔣政權(quán)和國民政府,另組投降日本的傀儡偽政府之后才做成了漢奸——這還是由于日軍戰(zhàn)事不利才促成此事的。由此可見日本人對于漢奸是需要什么樣的條件了,這頂帽子不是什么人可以戴上的。但是按照王明、康生之流的邏輯來分析,日本人反倒認(rèn)為陳獨(dú)秀的賣國資本比、還要大,于是就特別花日元去收買這個(gè)尚坐在牢房里的,政治上早已失勢,軍事上更加毫無影響力的共產(chǎn)黨中的反對派了。
抗日戰(zhàn)爭期間,在對待陳獨(dú)秀的問題上,國民黨反較共產(chǎn)黨客觀,陳之所以能獲釋,首先是當(dāng)局肯定了他“愛國情殷”的民族立場和“深自悔悟”的服刑態(tài)度,并且還得到了胡適和張伯苓二人出名保釋。當(dāng)然陳獨(dú)秀絕不會(huì)承認(rèn)悔改的,因?yàn)樗麖膩頉]有承認(rèn)自己有罪,他出獄以后立即公開表示:“愛國誠未敢自夸,悔悟則不知所指”(1937年8月25日致上海《申報(bào)》編輯部信)。
剛剛出版的2005年修訂版《魯迅全集》關(guān)于寫信給魯迅的托派“陳××”即陳仲山的注釋最后有這樣一句說明:“抗日戰(zhàn)爭期間在上海因從事抗日活動(dòng)被日軍捕殺。”(見第6卷P.610注[3])學(xué)術(shù)界給出這樣一個(gè)珍重歷史、還原歷史的公正說明,糾正中共黨史上對于一個(gè)托派的錯(cuò)誤結(jié)論,竟然花了七十年!而且,這還僅僅是對于一個(gè)人物的注釋而非對于整個(gè)事件的說明,只要馮雪峰所寫的這篇《答托洛斯基派的信》還收入在《魯迅全集》中,左翼文學(xué)上的這一大公案就不能說已經(jīng)得到了完全解決。
由于當(dāng)年魯迅心中郁積著比編自己的文集更大的憂慮,他的生命留給他的時(shí)間使他無法反思托派一類的問題了,他的迷惘與無奈更多的反映在他對于未來的悲觀情緒之中。他早就曾對人說:“倘當(dāng)崩潰之際,竟尚幸存,當(dāng)乞紅背心掃上海馬路耳。”(1934.4.30致曹聚仁信)魯迅曾譯介過許多俄羅斯同路人作家,他們的命運(yùn)他是很清楚的,在“左聯(lián)”成立大會(huì)上,他還提醒他的青年盟友們應(yīng)以俄羅斯同路人作家為前車之鑒;可是,晚年的他卻將自己實(shí)際上已經(jīng)擺在了一個(gè)同路人作家的位置上了。“左聯(lián)”成立之前,他寫了一篇《文藝與政治的歧途》(1927)的文章,其中寫道:“文藝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兩者之間,倒有不安于現(xiàn)狀的同一。惟政治是要維持現(xiàn)狀,自然和不安于現(xiàn)狀的文藝處在不同的方向。”他這話的意思是分著革命前和革命之后的,他認(rèn)為政治家在獲得權(quán)力前與文藝家之間是有著“不安于現(xiàn)狀的同一的”,但在取得政權(quán)之后,就與文藝家處在不同的方向了。政治家是要極力的維護(hù)自己的既得利益,維持現(xiàn)狀,文藝家卻是時(shí)刻觸著了感覺靈敏的神經(jīng),時(shí)刻不能安于這現(xiàn)狀的,于是要反抗現(xiàn)實(shí),因此文藝家與政治家不可避免的要發(fā)生沖突。可是魯迅沒有料到,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之時(shí),文藝家就已經(jīng)感到壓迫了。但是他哪里還會(huì)知道早在幾年前,柔石等“左聯(lián)”五作家只是因?yàn)榉磳δ箍迫送趺鞯臉O端專橫的政治路線,在去參加黨內(nèi)的一次秘密會(huì)議時(shí),被人泄密出賣而慘遭殺害的這一借刀殺人的真相呢?生前的事有許多都不知道,身后的事情就更不可能知道了。我們只能預(yù)料,假如他的壽命更長一些,活到了五十年代,他就可以看到過去“左翼”陣容的內(nèi)部斗爭的殘酷延續(xù)了,他必須面對一個(gè)及其悲慘的現(xiàn)實(shí),他的朋友胡風(fēng)、馮雪峰、丁玲、聶紺弩、蕭軍等等,無一幸免的一個(gè)一個(gè)遭到清算,全被打成了反革命分子或右派分子,或被投入死牢,或遭流放服苦役,或被群眾管制,而且他自己也不能保證沒有滅頂之災(zāi)。毫無疑問,他的心胸將一定比寫《答徐懋庸》的公開信時(shí)更為褊狹、更為憤怒——實(shí)際上當(dāng)年由馮雪峰起草的《答徐懋庸并關(guān)于抗日統(tǒng)一戰(zhàn)線問題》一文,在當(dāng)時(shí),應(yīng)該說還是給予他的論敵很“留情面的一棍”的了——然而從二十世紀(jì)五十年代開始直至七十年代末,中國已經(jīng)更加變成了無聲的中國,即使是魯迅,“連‘雜感’也被‘放進(jìn)了應(yīng)該去的地方’時(shí)”,他也就“只有‘而已’而已!”了。
“左聯(lián)”的解散,左翼作家內(nèi)部尖銳的宗派主義幫派斗爭,給予晚年魯迅的刺激是極大的,由于教訓(xùn),也由于時(shí)局,由于大環(huán)境的變化,實(shí)際上他已經(jīng)開始漸漸對自己做出了調(diào)整。
首先是政治上的決定,不再與原上海地下黨左翼文藝界的領(lǐng)導(dǎo)、他稱之為“元帥”“奴隸總管”的人合作,拒絕參加他們所組織策劃的中國文藝家協(xié)會(huì),不論這將給他帶上什么樣的帽子。他已經(jīng)很想抽身事外,他曾跟馮雪峰說:“我成為破壞國家大計(jì)的人了”,“我真想休息休息”。(馮雪峰《有關(guān)1936年周揚(yáng)等人的行動(dòng)以及魯迅提出“民族革命戰(zhàn)爭的大眾文學(xué)”口號(hào)的經(jīng)過》,載《新文學(xué)史料》1972年第2期)在1936年7月17日寫給楊之華的信中已流露出更加急迫的心情:“本月底或下月初起,我想離開上海兩三個(gè)月,作轉(zhuǎn)地療養(yǎng),在這里,真要逼死人。”而此時(shí)離他去世已僅僅三個(gè)月,已幾乎走到生命的盡頭了。
同時(shí),他在寫作上也已經(jīng)做出了相應(yīng)的調(diào)整,他急于想把手頭上的一些事做一個(gè)了結(jié),暫時(shí)擱下“匕首”,重新回到創(chuàng)作的道路上來。他已經(jīng)意識(shí)到“左聯(lián)”時(shí)期他的論戰(zhàn)性文章,用于內(nèi)耗的時(shí)候更多,遠(yuǎn)不及五四時(shí)期有益于社會(huì)改造。他曾幾次跟馮雪峰談起過要寫一部關(guān)于四代知識(shí)分子的長篇小說,而且他還有寫一部中國文學(xué)史的夙愿希望完成。從事文學(xué)創(chuàng)作并不是說就放棄了斗爭反抗的精神,對于一個(gè)思想家來說,他的無論什么體裁的作品都是深刻的,對于社會(huì)都是具有沖擊力的,并不一定只能用“投槍”和“匕首”似的論戰(zhàn)性雜文才有實(shí)效。他臨終前寫的《死》留有七條遺言,其中的第五條說:“孩子長大,倘無才能,可尋點(diǎn)小事情過活,萬不可去做空頭文學(xué)家或美術(shù)家。”這豈止是對家屬的交代和對一個(gè)七歲孩子說的話,他已經(jīng)厭惡透了那些只會(huì)斗嘴皮、沒有創(chuàng)作、沒有思想、只會(huì)打棍子的文學(xué)批評(píng)家,他深深感到做這樣一種人,對于社會(huì)毫無益處,他甚至自己也不愿意再做批評(píng)一類的文字,與這種人為伍,他想要回到創(chuàng)作的道路上來,并且已經(jīng)開始這么做了。在他生命的最后數(shù)月里,他除了創(chuàng)作了多篇散文,如《關(guān)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我的第一個(gè)師父》、《半夏小集》、《這也是生活……》、《死》、《女吊》之外,他還于1935年底完成了他的第三本小說集《故事新編》,1936年初出版,這正是“左聯(lián)”解散時(shí)期;但是由于他突然去世,剛剛?cè)计鸬膭?chuàng)作欲望也就此熄滅了。
魯迅在《新青年》團(tuán)體解散后曾出現(xiàn)過彷徨和迷惘,那是一種強(qiáng)烈的求索精神的表現(xiàn),他將“路漫漫其修遠(yuǎn)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題寫在《彷徨》書前,正表達(dá)了他的這種強(qiáng)烈的追求真理的愿望。但是“左聯(lián)”解散以后,他已經(jīng)失去了彷徨寂寞的心境,他希望的是休息,擺脫被人逼死的氛圍。他最后得到的人生經(jīng)驗(yàn)是:“損著別人的牙眼,卻反對報(bào)復(fù),主張寬容的人,萬勿和他接近。”(《死》,1936.9)這也是他對于后人的一句極有針對性的箴言。
注釋:
①1932年12月1日陳獨(dú)秀致胡適信,見《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冊。
②見《胡適全集》第24卷《致陳獨(dú)秀(1933.11.2)》,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③《答陳獨(dú)秀(1920.12)》,《胡適全集》第23卷。
④見1921年1月26日胡適致、魯迅等同人的信。此信及以上所引陳獨(dú)秀和信均編入《中國出版史料(現(xiàn)代部分)》第一卷上冊,見《涉及〈新青年〉分化的幾封信》,山東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⑤1921年1月29日錢玄同致胡適信,《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
【參考文獻(xiàn)】
[1]魯迅全集(第6卷及書信等卷)[C].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81、2005.
[2]胡適全集(第23、24卷)[C].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3]胡適來往書信選[C].北京:中華書局,1979.
[4]胡適的日記[M].北京:中華書局,1985.
[5]涉及《新青年》分化的幾封信[A].中國出版史料(現(xiàn)代部分)·第一卷上冊[C].濟(jì)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1.
[6]王觀泉.“天火”在中國燃燒[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05.
[7]胡風(fēng).魯迅先生(1984年)[J].北京:新文學(xué)史料,1993,(1).
[8]鄭超麟回憶錄[M].北京:東方出版社,2004.
[9].我的回憶[M].北京:東方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