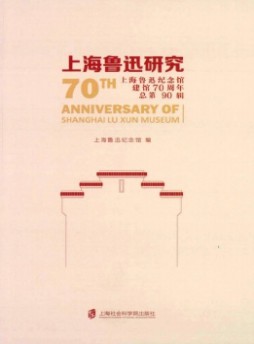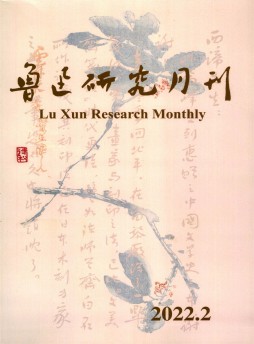魯迅基本走向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zhǔn)備了魯迅基本走向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diǎn)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xiě)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20世紀(jì)90年代以降,隨著冷戰(zhàn)時(shí)代的終結(jié),一方面各國(guó)之間的諸多壁壘逐漸被拆除,這使得魯迅作品在世界上的傳播渠道更為暢通;另一方面,蘇聯(lián)、東歐國(guó)家原先因意識(shí)形態(tài)緣由而形成的對(duì)魯迅的特殊興趣不復(fù)存在,對(duì)魯迅作品的譯介和研究進(jìn)入低谷。同樣也是因?yàn)槔鋺?zhàn)的結(jié)束,魯迅在亞、非、拉諸多第三世界國(guó)家的影響力日益縮小。但是在日本等遠(yuǎn)東國(guó)家和北美、西歐及其澳洲國(guó)家,研究魯迅作品的學(xué)術(shù)條件進(jìn)一步優(yōu)化,魯迅在這些國(guó)家的傳布出現(xiàn)了新的特點(diǎn)。本文將對(duì)20世紀(jì)90年代以降北美、澳洲和西歐①的魯迅研究狀況作初步的介紹和評(píng)價(jià)。
美國(guó)學(xué)者本時(shí)期發(fā)表了大量闡釋魯迅思想和作品的論文,這些論文有的是登載在學(xué)術(shù)刊物上,有的是被收錄在論文集里。在90年代初,黃維宗(音譯)的論文《無(wú)法逃避的困境:〈阿Q正傳〉的敘述者和他的話語(yǔ)》,對(duì)《阿Q正傳》所作的敘事學(xué)分析,顯示了運(yùn)用結(jié)構(gòu)主義方法論闡釋文本的可行性。楊書(shū)慧(音譯)的《道德失敗的恐懼:魯迅小說(shuō)的互文本解讀》,借助西方新的閱讀理論,在魯迅作品之間建立起“互文”關(guān)系,使它們成為相互關(guān)聯(lián)的有機(jī)整體。90年代中期以后,美國(guó)的魯迅研究呈現(xiàn)出“眾聲喧嘩”的局面。華裔學(xué)者的魯迅研究成績(jī)相當(dāng)突出,老一輩學(xué)者林毓生繼續(xù)關(guān)注魯迅思想的矛盾性,他的論文《魯迅?jìng)€(gè)人主義的性質(zhì)與含義——兼論“國(guó)民性”問(wèn)題》從魯迅1925年5月30日寫(xiě)給許廣平的一封信談起。在這封信中,魯迅說(shuō)自己的思想有許多矛盾,“人道主義與個(gè)人主義這兩種思想”在他身上“消長(zhǎng)起伏”著。林毓生動(dòng)用自己治思想史出身的知識(shí)儲(chǔ)備,證明在西方思想史上,人道主義與個(gè)人主義并無(wú)沖突,相反倒是具有相輔相成的關(guān)系。那么為什么這兩種“主義”在魯迅身上會(huì)發(fā)生沖突呢?經(jīng)過(guò)考證,林毓生發(fā)現(xiàn)《兩地書(shū)》鉛印本對(duì)原信作了刪改,魯迅在原信中說(shuō)的是“人道主義”與“個(gè)人無(wú)治主義”的沖突,“個(gè)人無(wú)治主義”即是無(wú)政府主義,與“個(gè)人主義”差別很大。那么魯迅為什么在信件出版時(shí)要作改動(dòng)呢?林毓生分析道,魯迅“一方面有‘安那其個(gè)人主義’的沖動(dòng),另一方面又覺(jué)得那是不負(fù)責(zé)任的‘毀滅’之路;一方面他仍不能不受人道主義的感動(dòng),但另一方面,他又感到這種沒(méi)有條件的‘大愛(ài)主義’在現(xiàn)實(shí)世界上行不通,在這種思想困境中,難免順著自己寫(xiě)文章的習(xí)慣做一點(diǎn)修辭上的工作了”。
接著,林毓生在論文中開(kāi)始討論魯迅的改造國(guó)民性問(wèn)題,他認(rèn)為魯迅在此問(wèn)題上走向了“邏輯的死結(jié)”。首先,“國(guó)民性”分析范疇具有很強(qiáng)的決定論傾向:假如中國(guó)的一切都是由國(guó)民性決定,那么無(wú)論歷史如何變遷,中國(guó)人還是中國(guó)人,其本質(zhì)是不會(huì)變的;其次,國(guó)民性到底是中國(guó)問(wèn)題的原因還是后果也說(shuō)不清楚。于是難免就走向邏輯死胡同:“一個(gè)在思想與精神上深患重疴的民族,如何能認(rèn)清重疴的基本原因是它的思想與精神呢?”魯迅思想陷入困境,在日本侵華后,作為愛(ài)國(guó)者的魯迅必須采取政治立場(chǎng),“而中國(guó)馬列主義已經(jīng)提出了一套革命的計(jì)劃與步驟,于是他便在未對(duì)它做深切研究之前,成為共產(chǎn)革命的同路人”。林毓生對(duì)魯迅思想困境及其衍變路徑的闡釋自然只是一家之言,但他的研究方法比較新穎,他提出的問(wèn)題具有挑戰(zhàn)性,值得魯迅研究者關(guān)注。
唐小兵的論文《魯迅的〈狂人日記〉和中國(guó)的現(xiàn)代主義》論述了魯迅創(chuàng)作的第一篇白話小說(shuō)對(duì)中國(guó)現(xiàn)代主義文學(xué)的開(kāi)創(chuàng)性貢獻(xiàn)。王德威的《魯迅、沈從文與砍頭》探討兩位中國(guó)現(xiàn)代文學(xué)大師不同的砍頭描寫(xiě)方式,以及不同砍頭描寫(xiě)方式背后蘊(yùn)含的道德、美學(xué)尺度。王德威認(rèn)為,魯迅在砍頭場(chǎng)景中看出中國(guó)的社會(huì)民心和中國(guó)的道統(tǒng)象征不可收拾的土崩瓦解;沈從文面對(duì)同樣的場(chǎng)面,卻試圖從文字的寓言層次,提供療傷彌縫的可能。魯迅在身體斷裂、意義流失的黑暗夾縫間,竟然發(fā)展出一種不由自主的迷戀。王德威在論文最后總結(jié)道:“五四以后的作家多數(shù)接受了魯迅的砍頭情結(jié),由文學(xué)‘反映’人生,力抒憂國(guó)憂民義憤。他們把魯迅視為新一代文學(xué)的頭頭。沈從文另辟蹊徑,把人生‘當(dāng)作’文學(xué),為他沒(méi)頭的故事找尋可以接上的頭。因此,他最吊詭的貢獻(xiàn),是把五四文學(xué)第一‘巨頭’——魯迅的言談敘事法則,一古腦而地砍將下來(lái)。他的文采想象,為現(xiàn)代小說(shuō)另起了一個(gè)源頭,而他對(duì)文學(xué)文字寓意的無(wú)悔追求,不由得我們不點(diǎn)頭。”
王德威寫(xiě)得“頭頭”是道,的確顯示了他恣肆的思辨力,他曾經(jīng)在林毓生任教的威斯康辛大學(xué)麥迪遜校區(qū)攻讀比較文學(xué)博士學(xué)位,對(duì)該校歷史系前輩林毓生的學(xué)術(shù)理路應(yīng)該比較熟悉,這兩位華裔學(xué)者的論著都顯示出突出的思辨能力。但他們的學(xué)術(shù)論著都存在這樣的問(wèn)題,即他們總是預(yù)先設(shè)定一個(gè)前提(也許他們不愿承認(rèn)),在林毓生那里是設(shè)定魯迅和陳獨(dú)秀、胡適等五四思想家都有中國(guó)傳統(tǒng)的“借思想、文化以解決問(wèn)題的方法”(thecultural-intellectualisticapproach),由此證明他們的反傳統(tǒng)是陷入了困境;在王德威這里是預(yù)設(shè)魯迅與沈從文的寫(xiě)作有著質(zhì)的區(qū)別,再根據(jù)這一預(yù)設(shè)去尋找兩人的差異。然而,魯迅與沈從文的思想和創(chuàng)作既顯示了差別,又具有共同取向(新加坡大學(xué)教授王潤(rùn)華對(duì)魯迅與沈從文共同性有過(guò)研究)。總之,王德威就魯迅和沈從文提出了一系列新穎的見(jiàn)解,但他的論證方法存在著的問(wèn)題決定了他的觀點(diǎn)只能是一家之言。
張隆溪的《作為基督的革命者:魯迅作品中未確認(rèn)的拯救者》,是一篇力圖在革命話語(yǔ)與基督教話語(yǔ)之間尋找詮釋魯迅創(chuàng)作之可能性的論文,顯示了在社會(huì)歷史和意識(shí)形態(tài)話語(yǔ)之外魯迅研究的闊大空間。梅儀慈的《文本、互文本與魯迅、郁達(dá)夫、王蒙的自我表現(xiàn)》把三位中國(guó)現(xiàn)當(dāng)代作家放在一起,通過(guò)他們作品的互文本關(guān)系,探討中國(guó)五四以來(lái)文學(xué)的自我表現(xiàn)傾向。本頓·格瑞格的《魯迅、托洛斯基以及中國(guó)的托洛斯基主義》對(duì)學(xué)術(shù)史上爭(zhēng)議不斷的魯迅和托洛斯基文藝思想關(guān)聯(lián)問(wèn)題作了深入的考察,確認(rèn)了兩人之間實(shí)際存在的關(guān)系。岳剛(音譯)的《魯迅與食人主義》[9]是研究魯迅對(duì)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中的“食人主義”批判立場(chǎng)的文章,也展示了魯迅作品對(duì)“吃人”主題的藝術(shù)表現(xiàn)。
進(jìn)入21世紀(jì)后,美國(guó)的魯迅研究者繼續(xù)保持著高度的學(xué)術(shù)熱情,寫(xiě)出了不少論文。卡迪斯·尼古拉斯撰寫(xiě)的論文《作為審美觀照的散文詩(shī):魯迅〈野草〉研究》[10]從美學(xué)視角探討了魯迅《野草》的意蘊(yùn)和創(chuàng)造力。施書(shū)梅(音譯)的論文《進(jìn)化主義與實(shí)驗(yàn)主義:魯迅與陶晶孫》[11],抓住中國(guó)思想史的進(jìn)化主義和實(shí)驗(yàn)主義兩大線索,對(duì)魯迅和同樣曾經(jīng)留學(xué)日本的創(chuàng)造社作家陶晶孫的思想和創(chuàng)作作了比較性的研究。保羅·福斯特撰寫(xiě)的論文《中國(guó)國(guó)民性的諷刺性膨脹:魯迅的國(guó)際性聲譽(yù)、羅曼·羅蘭評(píng)〈阿Q正傳〉及諾貝爾獎(jiǎng)》[12],對(duì)圍繞著《阿Q正傳》在世界上的傳播和影響問(wèn)題進(jìn)行了論評(píng)。《魯迅小說(shuō)的反諷和批判現(xiàn)實(shí)主義》[13]與《荒誕修辭學(xué):余華與魯迅創(chuàng)作中的荒謬性》[13]都是出自王班(音譯)之手的論文,前一篇從反諷角度研究魯迅小說(shuō)的批判現(xiàn)實(shí)主義特征,后一篇在小說(shuō)修辭學(xué)層面上對(duì)魯迅與當(dāng)代作家余華創(chuàng)作中的荒誕性作了創(chuàng)造性的闡釋。
再看專著方面,90年代以來(lái),美國(guó)出版了幾部專門研究魯迅的專著,一些研究中國(guó)現(xiàn)代文化和文學(xué)的學(xué)術(shù)著作也把魯迅當(dāng)作重點(diǎn)。寇志明的《詩(shī)人魯迅:魯迅舊體詩(shī)研究》由美國(guó)夏威夷大學(xué)出版社印行,將在介紹澳洲魯迅研究時(shí)再作評(píng)述。
J.R.普賽的《魯迅與進(jìn)化論》[14]分九章,在自中國(guó)近代以來(lái)進(jìn)化論的傳播之思想史背景下,研究了魯迅與進(jìn)化思想的關(guān)系。《魯迅與進(jìn)化論》的另一重要內(nèi)容是追蹤中國(guó)魯迅研究界如何評(píng)價(jià)、探討魯迅與進(jìn)化論關(guān)系的學(xué)術(shù)線索,并不時(shí)加入普賽個(gè)人的評(píng)價(jià)。普賽指出,青年魯迅的思想通常被中國(guó)學(xué)者說(shuō)成是受了達(dá)爾文主義及其分支學(xué)派社會(huì)達(dá)爾文主義的影響,但普賽引用美國(guó)著名的嚴(yán)復(fù)研究專家本杰明·施瓦茲(BenjaminSchwartz)的觀點(diǎn),認(rèn)為魯迅青年時(shí)代閱讀的嚴(yán)復(fù)所譯赫胥黎《天演論》實(shí)際上是“對(duì)社會(huì)達(dá)爾文主義的一個(gè)攻擊”。中國(guó)學(xué)者普遍把魯迅的思想說(shuō)成是經(jīng)歷了從進(jìn)化論到唯物論的演進(jìn),普賽反對(duì)這樣的描述,認(rèn)為“魯迅思想從來(lái)沒(méi)有經(jīng)歷過(guò)真正變化”,“真正的魯迅是一個(gè)真正的儒教徒”。認(rèn)為魯迅的思想幾乎是不變的觀點(diǎn)早在40年代就由日本的竹內(nèi)好提出過(guò),關(guān)于魯迅與儒家思想的關(guān)系至少林毓生在70年代就有所闡述。普賽在前人基礎(chǔ)上提出上述看法并無(wú)多大不妥,問(wèn)題在于普賽把這部專著的主要篇幅用于質(zhì)疑、批駁中國(guó)學(xué)者上,多少顯露了他精神深處還殘留著某種“冷戰(zhàn)”思維的痕跡,雖然普賽本人在理性上是想竭力避免重新陷入“冷戰(zhàn)”思維的陷阱的。
瑪麗·法夸爾的《中國(guó)的兒童文學(xué):從魯迅到》[15]是一部中國(guó)現(xiàn)當(dāng)代兒童文學(xué)史論專著,它的第二章《魯迅與兒童世界》研究了1903-1936年間魯迅關(guān)于兒童及其文學(xué)的寫(xiě)作情況,主要闡述了四個(gè)問(wèn)題:
一、魯迅和中國(guó)的西方兒童文學(xué)翻譯;
二、清末魯迅的早期兒童文學(xué)翻譯;
三、魯迅與五四前期的兒童文學(xué);
四、魯迅與五四后期的兒童文學(xué)。在這一章的結(jié)論部分,瑪麗·法夸爾指出,兒童及其文學(xué)的屬性一直為魯迅所關(guān)注,但魯迅的興趣總是集中在兒童及其文學(xué)所預(yù)示的中國(guó)社會(huì)未來(lái)的變化上,魯迅的這一思路對(duì)后來(lái)的中國(guó)兒童文學(xué)產(chǎn)生了深遠(yuǎn)的影響。愛(ài)德華·岡的《重寫(xiě)中國(guó):20世紀(jì)中國(guó)散文的風(fēng)格與創(chuàng)新》[16]雖然不是魯迅研究專著,但它對(duì)魯迅的《朝花夕拾》、《野草》以及雜文創(chuàng)作的情調(diào)和藝術(shù)都作了比較充分的闡釋,提出了一些較有見(jiàn)地的看法。
安德森的專著《現(xiàn)實(shí)主義的限制:革命時(shí)代的中國(guó)小說(shuō)》[17]第三章《魯迅、葉紹鈞與現(xiàn)實(shí)主義的道德阻礙》的第一節(jié)《魯迅:觀察的暴力》,對(duì)魯迅小說(shuō)的現(xiàn)實(shí)主義藝術(shù)形式及其道德困窘作了精彩的闡述。安德森舉日本教室里的幻燈片事件、小說(shuō)《示眾》的示眾場(chǎng)面和《阿Q正傳》的“犧牲儀式”為例,就魯迅作品對(duì)“觀看”暴力場(chǎng)面的現(xiàn)實(shí)主義藝術(shù)表現(xiàn)作了深入探討,他甚至分析出了這樣的意味,“在迫害者與受害者的目光碰撞中,暴力的走向被瞬間扭轉(zhuǎn):無(wú)論多么短暫,被看者(被粗暴地選中的示眾者)成了看客,而看客(中國(guó)庸眾,甚至也包括讀者自己)成了被看者”,“這一刻,讀者體驗(yàn)到,公眾的暴力恰恰植根于他們的行為在受害者心中激起的恐懼”。[17]藉此,魯迅對(duì)自己的寫(xiě)作和現(xiàn)實(shí)主義的藝術(shù)作了強(qiáng)烈的質(zhì)疑,“他暗示現(xiàn)實(shí)主義可能會(huì)使作家屈從于他們打算譴責(zé)的社會(huì)殘暴,在形式上描寫(xiě)壓迫者與被壓迫者間關(guān)系的現(xiàn)實(shí)主義敘述,有可能會(huì)被壓迫邏輯俘獲,最終只成為壓迫的復(fù)制”[17]。安德森竟然在現(xiàn)實(shí)主義文學(xué)對(duì)暴力的揭露性展示中,讀出了這種藝術(shù)表現(xiàn)方式與暴力制造者之間暗含的“同盟關(guān)系”,的確是深刻的誅心之論,這也是安德森的魯迅研究和中國(guó)現(xiàn)代文學(xué)研究的一個(gè)整體思路:藝術(shù)形式其實(shí)是隱含著道德因素的。安德森的這番研究,就把對(duì)文本的藝術(shù)分析與內(nèi)容分析結(jié)合起來(lái),使它們成為有機(jī)的整體。
華裔學(xué)者劉禾的《跨語(yǔ)際實(shí)踐:文學(xué)、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xiàn)代性》[18],是一部在海外中國(guó)學(xué)界尤其是中國(guó)現(xiàn)代文學(xué)研究界引起震動(dòng)的專著,她的主要觀點(diǎn)是:在中國(guó)的語(yǔ)境里,現(xiàn)代性觀念在數(shù)不盡的翻譯、復(fù)述中喪失了西方的本原意味,成為“翻譯中生成的現(xiàn)代性”。在該書(shū)的第二章《國(guó)民性理論質(zhì)疑》中,劉禾探討了魯迅的改造國(guó)民性思想與西方傳教士史密斯《中國(guó)人的氣質(zhì)》的關(guān)聯(lián),認(rèn)為“國(guó)民性”是一個(gè)隱含了西方霸權(quán)和優(yōu)越感的話語(yǔ),認(rèn)為魯迅“將傳教士的中國(guó)國(guó)民性理論‘翻譯’成自己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成為中國(guó)現(xiàn)代文學(xué)最重要的設(shè)計(jì)師”[18]。劉禾通過(guò)分析《阿Q正傳》的敘事,認(rèn)為魯迅創(chuàng)造了一個(gè)具有主體意識(shí)的敘事人,這使得小說(shuō)超越了史密斯的“支那人氣質(zhì)論”,“在中國(guó)現(xiàn)代文學(xué)中大幅改寫(xiě)了傳教士話語(yǔ)”。[18]劉禾大膽提出新見(jiàn)勇氣誠(chéng)然可嘉,但她把國(guó)民性問(wèn)題僅僅當(dāng)作西方傳來(lái)的“翻譯的國(guó)民性”,就比較偏頗了。中國(guó)現(xiàn)代國(guó)民性理論的確受到了西方的深深影響,但是中國(guó)就如英國(guó)、法國(guó)或其他國(guó)家一樣存在著自己的國(guó)民性,這也是不能輕易否認(rèn)的事實(shí);而魯迅創(chuàng)作中展開(kāi)的國(guó)民性批判乃是植根于中國(guó)的本土歷史與現(xiàn)實(shí),因此,魯迅的創(chuàng)作總能夠引起多數(shù)中國(guó)人的共鳴。
1998年華裔學(xué)者李天明在加拿大中國(guó)學(xué)家杜邁可(MichaelS.Duck)的指導(dǎo)下,以《魯迅散文詩(shī)〈野草〉主題研究》的論文在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xué)亞洲研究系獲得博士學(xué)位。2000年,李天明在自己的英文學(xué)位論文基礎(chǔ)上改寫(xiě)的著作《難以言說(shuō)的苦衷:魯迅〈野草〉探秘》在國(guó)內(nèi)出版[19],該書(shū)從社會(huì)政治批判、人生哲學(xué)思考以及情愛(ài)與道德責(zé)任的兩難這三個(gè)層面,對(duì)魯迅《野草》的主旨和內(nèi)涵進(jìn)行了比較深入的闡發(fā),書(shū)后所附《英語(yǔ)世界〈野草〉研究簡(jiǎn)介》,具有較高的史料價(jià)值。
與美國(guó)、加拿大同屬英語(yǔ)世界的澳大利亞在本時(shí)期出現(xiàn)了一些學(xué)術(shù)水準(zhǔn)較高的魯迅研究成果。G·戴維斯的長(zhǎng)篇論文《阿Q問(wèn)題的現(xiàn)代性》[20],考察了在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意識(shí)形態(tài)危機(jī)背景下,革命文學(xué)論爭(zhēng)中錢杏邨、馮乃超等人對(duì)魯迅的《阿Q正傳》的批判,并揭示出阿Q終極悲劇的現(xiàn)代性問(wèn)題。戴維斯認(rèn)為,小說(shuō)的“大團(tuán)圓”誘使“讀者去探求阿Q表面‘無(wú)意義的’生存背后所隱藏的深刻含義”,正是阿Q“這種‘存在的被拋入性’使讀者產(chǎn)生一種熱切的愿望:為阿Q的存在賦予意義”。[20]
原籍美國(guó)的寇志明(JonKowallis)任教于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大學(xué),在90年代推出了一批魯迅研究成果,他的著作《詩(shī)人魯迅:魯迅舊體詩(shī)研究》[21]由兩部分組成,一是介紹魯迅生平和文學(xué)創(chuàng)作情況的“導(dǎo)言”,主要向一般讀者提供魯迅舊體詩(shī)的時(shí)代和作者的傳記性背景,還就中國(guó)五四以來(lái)的舊體詩(shī)寫(xiě)作,以及魯迅的創(chuàng)作個(gè)性所受中國(guó)古典文學(xué)傳統(tǒng)影響等問(wèn)題作了學(xué)術(shù)探討。第二部分是寇志明翻譯的、按照編年體排列的魯迅現(xiàn)存64首舊體詩(shī)的英文譯本。寇志明的譯詩(shī)用英語(yǔ)詩(shī)歌的音韻來(lái)押韻,并使用了英詩(shī)的音步(音尺),使譯詩(shī)盡可能成為格律詩(shī),以傳達(dá)魯迅原詩(shī)的古典風(fēng)格。寇志明給每首詩(shī)都作了導(dǎo)讀,除了解釋詩(shī)篇的意蘊(yùn)外,還盡量引用魯迅的書(shū)信、他的文章的序言,以及親友的回憶中有關(guān)的說(shuō)明文字,為讀者理解詩(shī)篇提供參考。總之,這是一部有利于英語(yǔ)世界的讀者解讀魯迅舊體詩(shī)的著作。
寇志明的論文《節(jié)日之于魯迅:“小傳統(tǒng)”與國(guó)民身份認(rèn)同建設(shè)》[22]指出,魯迅在《朝花夕拾》、自傳性小說(shuō)以及其他回憶錄作品中,圍繞他過(guò)往的生活創(chuàng)造了一種“夢(mèng)幻式的氛圍”,魯迅的回憶中通常使用“節(jié)日”作為回歸過(guò)去生活的主要道具,在這些節(jié)日描寫(xiě)中,出現(xiàn)了一連串民間神靈和表演人神共慶的戲劇場(chǎng)面。論文考察了魯迅少年時(shí)代的習(xí)作《庚子送灶神即事》,以及他后來(lái)創(chuàng)作的《送灶日漫筆》、《祝福》、《社戲》、《五猖會(huì)》、《無(wú)常》等作品中的節(jié)日描寫(xiě)。論文的結(jié)論是:魯迅在寫(xiě)節(jié)日的時(shí)候,“都提供給我們一種多側(cè)面的民國(guó)時(shí)期對(duì)民族國(guó)家進(jìn)行確認(rèn)等一系列問(wèn)題的反思,而且也不經(jīng)意的對(duì)后來(lái)共產(chǎn)主義定義中國(guó)大眾文化的意圖進(jìn)行了反思”,“對(duì)魯迅來(lái)說(shuō),節(jié)日的儀式和戲劇更多是作為社會(huì)批評(píng)的比喻,而不是作為對(duì)俗文化在創(chuàng)造‘新’的民族文化中所占地位的肯定”[22]。寇志明還寫(xiě)有《魯迅與果戈理》[23]這樣的比較文學(xué)論文,對(duì)魯迅和果戈理的同題小說(shuō)《狂人日記》的意蘊(yùn)、人物和藝術(shù)諸方面進(jìn)行對(duì)照,比較了魯迅與他的俄國(guó)文學(xué)前輩創(chuàng)作的異同。
英國(guó)學(xué)者的魯迅研究成果數(shù)量不多,但顯示了穩(wěn)扎穩(wěn)打的求實(shí)精神。波尼·麥克道戈?duì)柡蛣P姆·勞撰寫(xiě)的《20世紀(jì)的中國(guó)文學(xué)》[24]屬于文學(xué)史著作,其中對(duì)魯迅的創(chuàng)作有較多的評(píng)述。在論及《野草》時(shí),該文學(xué)史指出,“這些散文詩(shī)融記事、諷刺、懷舊、夢(mèng)幻和短劇、打油詩(shī)等多種風(fēng)格和技法于一體”,“《野草》在主觀性、抒情性風(fēng)格的探索上作了罕見(jiàn)的嘗試”,“魯迅對(duì)‘黑暗力量’的執(zhí)迷構(gòu)成《野草》的基本線索”。[24]該文學(xué)史對(duì)于魯迅的小說(shuō)創(chuàng)作作了更充分的評(píng)價(jià),認(rèn)為魯迅的《狂人日記》“雖然從靈感和標(biāo)題上都受了果戈理的恩惠,但它是完全具有原創(chuàng)性的作品,它是中國(guó)第一篇同時(shí)使用文言和白話寫(xiě)作的小說(shuō),序言用文言寫(xiě)作暗示了這種語(yǔ)言的權(quán)威地位,而且文白并置暗示了《新青年》讀者群需要被啟蒙。當(dāng)然,該文學(xué)史也顯示了西方學(xué)者還未能完全擺脫把魯迅的小說(shuō)當(dāng)作是對(duì)中國(guó)現(xiàn)代社會(huì)的反映的這一傳統(tǒng)的分析模式,比如對(duì)《阿Q正傳》、《藥》等作品的闡釋,就基本把它們定位在對(duì)辛亥革命不徹底性的批判上,這恐怕也是受了中國(guó)國(guó)內(nèi)學(xué)術(shù)界庸俗社會(huì)學(xué)研究模式的影響。
卜立德在上一個(gè)時(shí)期就撰寫(xiě)了一些魯迅研究的論文,他70年代出版的周作人文藝思想研究專著也對(duì)魯迅多有述及,成為英國(guó)一位知名的中國(guó)現(xiàn)代文學(xué)研究專家。卜立德自80年代末以來(lái)到香港中文大學(xué)和香港城市大學(xué)等高校翻譯系任教,從事中國(guó)現(xiàn)代文學(xué)的翻譯和研究,撰寫(xiě)了一系列論文,關(guān)于魯迅的論文就有好幾篇。在《〈吶喊〉的骨干體系》一文中,卜立德對(duì)初版《吶喊》的十三篇小說(shuō)進(jìn)行了解讀,試圖勾勒這部小說(shuō)集的基本框架,他認(rèn)為《不周山》只是神話的改寫(xiě),《鴨的喜劇》、《兔和貓》、《社戲》幾篇實(shí)際為紀(jì)實(shí)文章,而《頭發(fā)的故事》、《端午節(jié)》、《白光》很少被人關(guān)注。卜立德對(duì)《吶喊》其他的小說(shuō)作了“新批評(píng)”式的細(xì)讀,讀出了一些獨(dú)特的意味,他認(rèn)為《藥》寫(xiě)墳?zāi)沟姆諊c其說(shuō)是和安特萊夫的作品接近,不如說(shuō)更接近法國(guó)作家繆塞《世紀(jì)兒懺悔錄》主人公向天呼喚的一節(jié),從所引的繆塞作品來(lái)看,卜立德說(shuō)的的確有些道理。認(rèn)為在《孔乙己》中由于敘述者抑制自己的同情態(tài)度,反而造成讀者對(duì)孔乙己的更大同情。認(rèn)為對(duì)于魯迅筆下那些被人壓迫,同時(shí)又互相欺騙和苛待的中國(guó)人來(lái)說(shuō),反諷可能是唯一的描寫(xiě)筆法。認(rèn)為魯迅的反諷是多樣的,“有時(shí)沉重,有時(shí)挖苦,有時(shí)開(kāi)玩笑,它隱藏著同時(shí)又揭示一種愛(ài)恨交纏的復(fù)雜感情,這給予他的杰作以感情的深度,是至今無(wú)人可比的”[25]。
卜立德的《魯迅的兩篇早期翻譯》對(duì)魯迅1903年留日時(shí)期嘗試翻譯的凡爾納的小說(shuō)《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的文本作了深度研究。魯迅這些譯本是從日文譯本轉(zhuǎn)譯而來(lái)的,而日譯本不是直接從法國(guó)作家凡爾納作品翻譯,而是從英譯本轉(zhuǎn)譯。作為從事中西翻譯研究的學(xué)者,卜立德精通英、法、漢、日等語(yǔ)言,由他來(lái)研究魯迅早期這兩篇譯文是比較合適的。卜立德從日本國(guó)會(huì)圖書(shū)館找到了凡爾納這兩篇小說(shuō)的部分日譯本,把他們與魯迅的漢譯本對(duì)讀,發(fā)現(xiàn)了很多問(wèn)題,原來(lái)日譯本對(duì)原著改動(dòng)很大,魯迅對(duì)日譯本也有所改譯。卜立德在魯迅翻譯的兩篇小說(shuō)、日譯本殘卷、法文原著之間作了精細(xì)的校讀,發(fā)現(xiàn)《月界旅行》的日本翻譯者對(duì)原著任意改編的情況很普遍,魯迅的譯本只是在日譯本基礎(chǔ)上加以修飾、整理、夸大,但章回體式的回目是魯迅加上去的。而在《地底旅行》翻譯過(guò)程中,魯迅加進(jìn)去了不少“敗筆”,尤其是對(duì)小說(shuō)對(duì)話的翻譯問(wèn)題較多,這對(duì)原著是一種“破毀”。卜立德是研究中西翻譯的行家,他當(dāng)然知道20世紀(jì)初年改譯外國(guó)文學(xué)作品是中國(guó)知識(shí)界的一種風(fēng)尚,林紓和梁?jiǎn)⒊S便改譯的外國(guó)作品在當(dāng)時(shí)影響很大。卜立德對(duì)于魯迅的翻譯水平總體評(píng)價(jià)不很高,但他寫(xiě)這篇論文不是為挑錯(cuò)而來(lái)的,他是把魯迅早期的譯本作為一種學(xué)術(shù)現(xiàn)象來(lái)探討,他提醒說(shuō):“原文和譯文之間這種出入給比較文學(xué)研究提供了寶貴的資料。”[26]
卜立德的《為豆腐西施翻案》屬于帶點(diǎn)“戲謔”色彩的論文,他主要是不滿中國(guó)大陸學(xué)術(shù)界和語(yǔ)文教育界把魯迅《故鄉(xiāng)》中的人物豆腐西施視為反面角色,他認(rèn)為這其實(shí)是一種誤讀。卜立德分析了造成誤讀的兩個(gè)原因:粗心的讀者以為,既然與作者姓名有一字相同之小說(shuō)敘述者“迅”不喜歡豆腐西施,那魯迅就不喜歡她;帶階級(jí)偏見(jiàn)的讀者認(rèn)為魯迅愛(ài)貧窮的閏土,不喜歡小市民豆腐西施。其實(shí)敘述者“迅”不是魯迅本人,豆腐西施也不比閏土道德低下,閏土見(jiàn)到“迅”恭敬地叫“老爺”,而豆腐西施見(jiàn)了“迅”仍然稱呼她的小名“迅哥兒”,還挖苦“迅”貴人健忘,可見(jiàn)她比閏土有勇氣面對(duì)發(fā)跡后的“迅”。而且她拿東西也是當(dāng)著“迅”的面拿,算不上偷。倒是閏土偷偷在灰堆里埋碗碟,敗壞了“迅”對(duì)他少年時(shí)代的良好印象。卜立德認(rèn)為豆腐西施接近魯迅雜文《阿金》中的主人公,她們顯得很潑,魯迅實(shí)際上對(duì)阿金式的“潑婦”有所贊賞,肯定她們的野氣和膽量。[27]
卜立德上述觀點(diǎn)未必都能夠說(shuō)服別人,真正讓人嘆服的是,作為一名英裔學(xué)者他能夠非常自如地運(yùn)用漢語(yǔ)寫(xiě)出上述論文,而且還能夠?qū)懙媚敲辞纹び哪O啾戎拢S多歐美和日韓中國(guó)學(xué)家由于對(duì)漢語(yǔ)掌握不夠嫻熟,寫(xiě)起漢語(yǔ)文章總帶“老外腔”。這當(dāng)然不是問(wèn)題的關(guān)鍵,關(guān)鍵是由于不精通漢語(yǔ),不少外國(guó)的中國(guó)漢學(xué)家讀不懂、看不透魯迅的作品,在他們的論著中就難免出現(xiàn)了一些誤讀。不過(guò),這也是跨文化交流中必然出現(xiàn)的事,想完全避免也難。
2002年,卜立德用英文寫(xiě)作的《魯迅正傳》在香港中文大學(xué)出版社刊行[28],該傳記分17章敘寫(xiě)魯迅自出生到死亡的生命歷程,《魯迅研究月刊》登載過(guò)黃喬生翻譯的這部傳記的第十章[29]。卜立德在傳記的前言中交代,鑒于過(guò)往的魯迅研究專著對(duì)魯迅稱贊的占絕對(duì)多數(shù),他準(zhǔn)備采取一種公正、公平的態(tài)度來(lái)寫(xiě)魯迅?jìng)鳎瑧?yīng)該說(shuō)他基本完成了這一預(yù)設(shè)目標(biāo)。這部魯迅?jìng)鞒藬⑹霰容^平穩(wěn)、理論比較持平外,具體寫(xiě)法上也有自己的特色,正如黃喬生所言,卜立德“很注重使用細(xì)節(jié)和實(shí)證材料,也很注重傳主的生活環(huán)境的再現(xiàn)”[30],這種寫(xiě)法恐怕值得大陸學(xué)者借鑒,因?yàn)槲覀兊聂斞競(jìng)饔浿杏刑鄬?duì)時(shí)代風(fēng)云、社會(huì)背景的“宏大敘述”,而忘記了魯迅首先是一個(gè)有血肉的人,也是一個(gè)生存于日常生活中的人。
本時(shí)期法國(guó)的魯迅研究顯得步履維艱,原計(jì)劃出版的8卷本魯迅作品集因資金問(wèn)題未能出版,這對(duì)法國(guó)魯迅研究者來(lái)說(shuō)應(yīng)該算是一次不小的挫折,但米歇爾·露阿等“魯迅小組”中的學(xué)者一如既往地?zé)釔?ài)和研究著魯迅。米歇爾·露阿給中國(guó)的刊物寄來(lái)《敬隱漁名字的來(lái)源》[31]這樣的考據(jù)性文章,解釋20年代最初把魯迅的《阿Q正傳》翻譯成法文的敬隱漁姓名的基督教背景,以及其姓名每一個(gè)字在基督教文化中的含義和象征,有較高的學(xué)術(shù)價(jià)值。
90年代中期,米歇爾·露阿為中國(guó)畫(huà)家裘沙、王偉君的《魯迅之世界全集》作序[32],她認(rèn)為裘沙、王偉君畫(huà)的《魯迅之世界》是另一種意義上的翻譯工作,比起把漢語(yǔ)的魯迅作品譯成法語(yǔ)并不會(huì)容易,這種特殊的翻譯“是兩種感覺(jué)方式之間的紐帶,兩種文化之間思想溝通的橋梁,它是一種超越國(guó)界的語(yǔ)言”[32]。她認(rèn)為裘沙、王偉君的畫(huà)面常常“象閃電一般將魯迅深刻的思想內(nèi)涵揭示在我們面前”,她感謝畫(huà)家辛勤的勞作使人們更容易走進(jìn)魯迅的精神世界。
法國(guó)出版的一部名為《浪漫的現(xiàn)代中國(guó):1918-1949》[33]的著作,以中國(guó)現(xiàn)代文學(xué)作品為研究對(duì)象,描繪20世紀(jì)前期中國(guó)人的精神生活,其中對(duì)魯迅的創(chuàng)作多有闡述,值得注意。
德語(yǔ)世界對(duì)魯迅的研究并不寂寞,一些熱愛(ài)魯迅的學(xué)者在默默做著研究工作,奉獻(xiàn)了自己高質(zhì)量的精神產(chǎn)品。瑞士學(xué)者馮鐵的論文《略論中國(guó)現(xiàn)代文學(xué)中的時(shí)間運(yùn)用——以魯迅等作家為例》[34],引用了魯迅的小說(shuō)、書(shū)信、日記的時(shí)間記錄方式,對(duì)其特點(diǎn)進(jìn)行討論,試圖探尋民國(guó)時(shí)期中國(guó)的時(shí)間記錄方法及其所包含的歷史意識(shí)、象征意義,認(rèn)為魯迅的《狂人日記》日期記錄沒(méi)有任何線索,時(shí)間的進(jìn)行是模糊而不規(guī)則的,這實(shí)際上符合精神病人對(duì)時(shí)間的感應(yīng)。
1994年在瑞士聯(lián)合出版社出版了六卷本《魯迅選集》,選集的主持者是德國(guó)沃爾夫?qū)ゎ櫛颍珜?xiě)了長(zhǎng)篇后記[35],后記對(duì)他本人學(xué)習(xí)漢語(yǔ),走向魯迅作品翻譯和研究之路的歷程作了勾勒,對(duì)德國(guó)學(xué)者翻譯魯迅作品基本情況作了回顧和評(píng)價(jià),對(duì)魯迅的小說(shuō)、散文、雜文等各類作品作了細(xì)讀,中間穿插了對(duì)歐美魯迅研究成果的評(píng)價(jià)。顧彬說(shuō)西方魯迅研究經(jīng)歷了波折后,不少學(xué)者在1989年之后終于確定了這樣的研究原則:“既反對(duì)視魯迅為純粹革命者的正統(tǒng)觀點(diǎn),也反對(duì)將魯迅視作虛無(wú)主義者的反教條主義的觀點(diǎn)”,“我們?cè)噲D在兩個(gè)極端之間尋求一種折中的理解”。[35]顧彬指出,“時(shí)代精神的批判性分析無(wú)疑是貫穿魯迅作品始終的一條紅線,而長(zhǎng)久地堅(jiān)持獨(dú)立性也使作家付出了代價(jià):寂寞、厭煩或者說(shuō)是無(wú)聊的苦悶”糾纏著他;魯迅作品“應(yīng)該被看作是關(guān)于希望之可能與否以及憂郁的藝術(shù)的一種疏離的、自嘲的話語(yǔ)”。[35]在分析魯迅散文創(chuàng)作的藝術(shù)時(shí),顧彬深刻地指出,“離題是魯迅散文至今未被認(rèn)識(shí)的一個(gè)風(fēng)格技巧:不追隨某一個(gè)既定的主題,作者運(yùn)筆是如此地散漫,以致于失去了他的描寫(xiě)對(duì)象”[35],他認(rèn)為散文化的小說(shuō)《社戲》就是這樣作品的典型。
2001年德國(guó)法蘭克福的彼得·朗格公司用德語(yǔ)出版了《魯迅:中國(guó)“溫和”的尼采》[36]一書(shū),它的作者張釗貽是澳大利亞昆士蘭大學(xué)的教師(他在1987年出版過(guò)英文著作《尼采和魯迅思想的發(fā)展》),該書(shū)分五章論述問(wèn)題:
一、尼采到東方的旅程;
二、奴隸價(jià)值的重估;
三、尼采的反政治性和精神激進(jìn)主義;
四、尼采的永恒的“民族性”改革;
五、魯迅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中的尼采影響。該書(shū)最后的結(jié)論是:“通過(guò)融和現(xiàn)代西方和中國(guó)傳統(tǒng)中的‘積極力量’,魯迅把尼采帶給中國(guó),把中國(guó)帶向世界。”[37]
90年代初以來(lái),冷戰(zhàn)格局的終結(jié)使西方魯迅研究進(jìn)入了良性發(fā)展階段,上一時(shí)期魯迅研究論著中時(shí)常現(xiàn)身的二元對(duì)立冷戰(zhàn)思維逐步消失,僅僅把魯迅作品當(dāng)作觀照中國(guó)現(xiàn)代社會(huì)之范文的研究理路逐漸退出學(xué)術(shù)界,從藝術(shù)本體、審美特性、文化心理等層面研究魯迅的文本和精神結(jié)構(gòu)成為基本學(xué)術(shù)趨向,尤其是對(duì)魯迅作品作藝術(shù)本體的闡釋之風(fēng)氣日益濃厚,這一切都表明:魯迅越來(lái)越被當(dāng)作文學(xué)家看待,表明魯迅研究在這些國(guó)家正日益走向深化。希望90年代以來(lái)西方魯迅研究的學(xué)術(shù)思維、觀察視角、研究方法,能夠?yàn)閲?guó)內(nèi)的魯迅研究者提供參考和啟發(fā)。
注釋:
①本文把這三個(gè)區(qū)域的國(guó)家統(tǒng)稱為西方國(guó)家。
【參考文獻(xiàn)】
HuangWeizong.TheInescapablePredicament:TheNarratorandHisDiscoursein"TheTrueStoryofAhQ"[J].ModernChina,16,4(October1990).
YangShuhui.TheFearofMoralFailure:AnIntertextualReadingofLuHsun''''sFiction[J].TamkangReview,21,3(1991).
林毓生.魯迅?jìng)€(gè)人主義的性質(zhì)與含義——兼論“國(guó)民性”問(wèn)題[J].香港,二十一世紀(jì),1992,(8).
TangXiaobin.LuXun''''s"DiaryofaMadman"andaChineseModernism[J].PMLA,107,5(1992).
DavidDer-weiWang.LuXun,ShenCongwen,andDecapitation[A].InX.TangandL.Kang,eds.Politics,Ideology,andLiteraryDiscourseinModernChina:TheoreticalInterventionsandCulturalCritique[M].Durham:DukeUP,1993.
ZhangLongxi.RevolutionaryasChrist:TheUnrecognizedSaviorinLuXun''''sWorks[J].ChristianityandLiterature45:1(Autumn1995).
Yi-tsiMeiFeuerwerker.Text,Intertext,andtheRepresentationofSelfinLuXun,YuDafu,andWangMeng[A].InE.WidmerandD.Wang,eds.,FromMayFourthtoJuneFourth:FictionandFilminTwentieth-CenturyChina[M].Cambridge:HUP,1993.
BentonGregor.LuXun,LeonTrotsky,andtheChineseTrotskyists[J].EastAsianHistory7(1994).
[9]YueGang.LuXunandCannibalism[J].InTheMouththatBegs:Hunger,Cannibalism,andthePoliticsofEatinginModernChina[M].Durham:DukeUniversityPress,1999.
[10]KaldisNicholas.TheProsePoemasAestheticCognition:LuXun''''sYecao[J].JournalofModernLiteratureinChinese3,2(Jan.2000).
[11]ShihShu-mei.EvolutionismandExperimentalism:LuXunandTanJingsun[A].InShi,TheLureoftheModern:WritingModernisminSemicolonialChina,1917-1937[M].Berkeley:UCPress,2001.
[12]PaulB.Foster.TheIronicInflationofChineseNationalCharacter:LuXun''''sInternationalReputation,RomanRolland''''sCritiqueof''''TheTrueStoryofAhQ,''''andtheNobelPrize[J].ModernChineseLiteratureandCulture13,1(Spring2001).
[13]WangBan.IronyandSocialCriticisminLuXun''''sFiction[A].RhetoricoftheAbsurd:theGrotesqueinYuHuaandLuXun[A].InWang,NarrativePerspectiveandIronyinSelectedChineseandAmericanFiction[M].Lewiston,NY:EdwinMellen,2002.
[14]JamesReevePusey.LuXunandevolution[M].StateuniversityofNewYorkpress,1998.
[15]MaryAnnFarguhar.Children''''sliteratureinChina:FromLuXuntoMaoZedong[M].M.E.Sharpe,Armonk,NewYork,1999.
[16]EdwardGunn.RewritingChinese:styleandinnovationintwentiethcenturyChineseprose[M].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91.
[17]MarstonAnderson.Thelimitsofrealisim:chinesefictionintherevolutionaryperiod[M].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90.現(xiàn)實(shí)主義的限制:革命時(shí)期的中國(guó)小說(shuō)[M].中譯本(姜濤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
[18]LydiaH.Liu.Translingualpractice:literature,nationalculture,andtranslatedmodernity-China,1900-1937[M].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95.跨語(yǔ)際實(shí)踐:文學(xué)、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xiàn)代性[M].中譯本(宋偉杰等譯).北京:三聯(lián)書(shū)店,2002.
[19]李天明.難以言說(shuō)的苦衷:魯迅《野草》探秘[M].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0.
[20]Davies,Gloria.TheProblematicModernityofAhQ[J].ChineseLiteratureEssaysArticlesReviews13(1991).
[21]JonKowallis.TheLyricalLuXun:aStudyofHisClassical-StyleVerse[M].HawaiiUniversityPress,1996.
[22]JonKowallis.FestivalsforLuXun:The"LesserTradition"andNationalIdentityConstruction[J].ChinoperlPapers:ChineseOralandPerformingliterature20-22(1997-99).
[23]JonKowallis.LuXunandGogol[J].TheSovietandPost-SovietReview,27:2(2000).
[24]BonnieS.McDougall,KamLouie.TheliteratureofChinainthetwentieth-century[M].HurstandCompany,London,1997.
[25]卜立德.《吶喊》的骨干體系[J].尹慧珉譯.魯迅研究月刊,1992,(8).
[26]卜立德.魯迅的兩篇早期翻譯[J].魯迅研究月刊,1993,(1).
[27]卜立德.為豆腐西施翻案[J].魯迅研究月刊,2002,(5).
[28]DavidE.Pollard.TheTrueStoryofLuXun[M].HongKong,TheChineseUniversityPress,2002.
[29]卜立德著,黃喬生譯.轉(zhuǎn)變中的魯迅:廈門和廣州[J].魯迅研究月刊,2003,(3).
[30]卜德著,黃喬生譯.轉(zhuǎn)變中的魯迅:廈門和廣州“譯后記”[J].魯迅研究月刊,2003,(3).
[31]米歇爾·露阿.敬隱魚(yú)名字的來(lái)源[J].魯迅研究月刊,1995,(6).
[32]米歇爾·露阿.《魯迅之世界全集》作序[J].魯迅研究月刊,1996,(1).
[33]ZhangYinde.Leromanchinoismoderne1918-1949[M].Paris:PressesUniversitairesdeFrance,1992.
[34]馮鐵.略論中國(guó)現(xiàn)代文學(xué)中的時(shí)間運(yùn)用——以魯迅等作家為例[J].魯迅研究月刊,1998,(11)(譯者李良元).
[35]沃爾夫?qū)ゎ櫛蛑赫棺g.“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魯迅文集〉后記[J].魯迅研究月刊,2001,(5).
[36]Chiu-yeeCheung(ZhangZhaoyi).LuXun:theChinese"Gentle"Nietzsche[M].Frankfurt,etal.:PeterDang,2001.
[37]馮鐵著,蕭婉譯.書(shū)評(píng)三篇·《魯迅:中國(guó)“溫和”的尼采》[J].魯迅研究月刊,200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