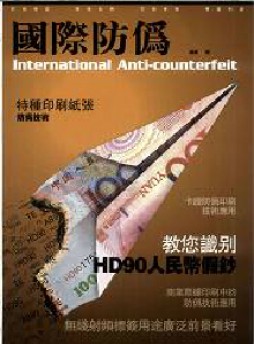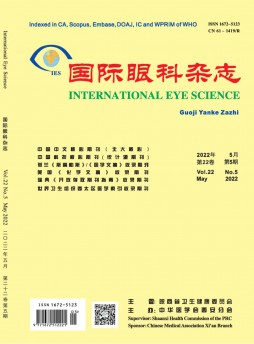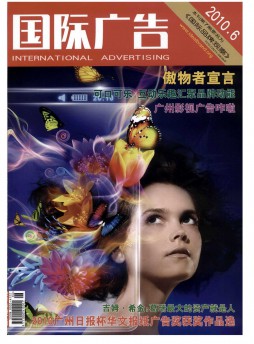論國際法學教育的發展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論國際法學教育的發展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在這一階段,國立北京大學、國立中央大學、朝陽大學、東吳大學、北京法政專門學校的法學教育中似最具規模、影響力最盛。節取上述各校的課程設置,以及20世紀40年代國民政府所修正的法律學系科目表,可有如下觀察:
首先,國際法課程在得到一如既往的重視的同時,也在教學上有了更為精細的授課安排。除在課程中普遍將國際法區分為國際公法與國際私法獨立授課外,一些學校也進一步將國際公法區分為平時國際法與戰時國際法在不同學年各自講授。雖然這種課目劃分并非此階段的新興現象,但更多學校對這一國際法課程設置的采用,既是國人對國際法學的認知更為系統全面之體現,也意味著法科學校愿意給予國際法更為充分的學習時間,顯示出對國際法教育有了更高的評估與偏重。如,國立北京大學20世紀20年代的法學專業課程中,在第二、三學年開設國際公法,而在第四學年開設國際私法。國立中央大學從第三學年劃分組系,而無論是司法組、行政法組,還是法學組,都將在這一學年開設國際公法課程,而在第四學年開設國際私法課程。其中,國立北京大學的國際公法課程更細分為平時國際公法與戰時國際公法,前者講授于第二學年,后者則講授于第三學年。
其次,國際法課程得到授課時數或年限上的較好保證。在多數學校,國際法課的授課年限至少為一年。如,中央大學法學院為三個不同組系所安排的國際公法授課時間均為一年,即使是列為選修課目錄中也未縮減。東吳大學的國際公法課程的學習年限也為一年,且在那一學年中所占學分最高。較之同校一些僅開設半年的基本法學課程,如中國憲法、中國刑事訴訟法、中國刑法總則、中國民法總則等等,國際法一年的學習時限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出其在中國法學教育中所占之地位。而在北京大學法科,由于平時國際法與戰時國際法的分開授課,實際也分配給國際公法兩年的學習時間。
最后,國際法出現從法學教學科目向法學教育專業上升的跡象。作為法學教育的必要構成,清末以來的國際法教育一直是作為教學科目之一得以重視并漸為發展。而至20世紀40年代,按國民政府教育部1945年修正之法律學系科目表所示,中國國際法教育有了性質與地位的又一次提升。據此科目表,除共同必修科目以外,法律系可采兩種學分制度,一為混分制,二為分組制。在分組制教學中,四大組系分別為:司法組、行政法學組、國際法學組、理論法學組。在這種分組制的科目列表中,對于司法組、行政法學組以及理論法學組而言,國際法仍作為共同必修課之一門;但對于國際法學組而言,國際法教育不再單單體現于一或兩門法學課程,而成為了一個法科教育的專業或培養方向。國際法教育由此開始了從法學學科下的一門課程向高等教育的一個獨立學科的演進軌跡。
國際法學師資構成的演變與充實
早期從事中國法學教育的多為西方傳教士,丁韙良無疑是在中國教授國際法課程的第一人。至清末修律,大量外國法律專家被聘來華執教,日本學者則成為其中之最。據載,清末京師法政學堂、京師法律學堂、直隸法政學堂、山西法政學堂等22所法政專門學堂均有延請日本教師,達311人之多。以京師法律學堂的課程開設為例,包括法學通論、憲法、國法學、刑法、民法、商法、法院編制法、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破產法等在內的全部法學主干課程都由日本學者擔綱。其中,擔任國際法教學的為巖井尊聞,而教授國際私法的則為志田鉀太郎[2]116,726。時至民國,國際法教學的師資隊伍開始出現明顯的本土化趨勢。隨著法科留學生的陸續回國,以及中國各類法科學校所培養人才的日漸出爐,民國時各大學法科或專門法政學校中執教的中國教師越來越多,國際法師資隊伍中的中國教師比例也日益提高,至20世紀30年代后已經開始占據主導地位。以當時法學教育界享譽盛名的“北朝陽南東吳”為例。從民國元年發展至20世紀20年代前后,朝陽大學的法學教員中盡管仍有岡田朝太郎、巖谷蓀藏等外國教師,但其主要教學任務已交由中國教師來完成,所聘請者不乏當時中國各知名法家,如余棨昌、鐘賡言、程樹德、陳鎬生、王家駒、李懷亮等等。最初在該校教授國際公法的為來自日本早稻田大學的巽來次郎,但據1917年《教育部視察朝陽大學報告》,當時亦有中國教員承擔此門課程的講授。報告中提及,檢查當時正逢中國教師錢泰在講授國際公法課程,報告評價其教學為“講解詳明,學生尚能注意”[3]464。而作為與朝陽大學齊名的又一著名私立高校,東吳大學的本土師資也得到明顯充實。由于創建東吳大學法科的美國人蘭金本是律師出身,為在中國培養具有現代專業素養的司法人才,東吳大學最初所聘教員都為實務界人士,并有不少外籍專家,如“大美國按察使衙門”的羅炳吉(CharlesS.Lobingier)。而隨著學校的擴充,如董康、吳經熊、梅華銓、張君勵等中國法界名人都陸續受聘開始于東吳大學法科執教。至20世紀30年代,在東吳大學法學院執教各主干課程的人員中,除教授英美法的薩萊德(GeorgeSellett)與教授國際公法的路義斯(Robert.E.Lewis)外,其他如法理學、憲法學、羅馬法、法制史、刑法、刑事訴訟法、民法、民事訴訟法等各門課程的授課教師均為中國人。而在路義斯外,其他擔任國際公法教學的都為中國教師,如梁鋆立、姚啟胤、夏晉麟、倪征燠。就當時在各校教授國際法的中國教師的學歷構成來看,其大部分都具有外洋留學背景。其中,小部分人求學于東洋日本,如周鯁生曾于1906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學留學,并在那里加入中國同盟會;更多人則選擇遠赴歐美,如在東吳大學教授國際法之錢泰就留學于法國巴黎大學,并獲博士學位。不過,這些后來活躍在中國國際法教育舞臺上的身影,留學前多已在國內研修過法律,往往同時具有中外兩方的法學教育背景。可以認為,對于曾積極參與過民國時期國際法教學研究的上述各人,留學是對其學識的提升與眼界的拓展,但這種收獲與國內法學教育所提供的有益導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息息相關。這也從又一側面印證了民國時期中國國際法教育的成長與收效。
國際法學教育對國際法理論研究繁盛之促成
外國著作或教材的翻譯無疑是中國國際法教學資料的第一來源。早在京師同文館開設國際法課程的最初,丁韙良主導下的一系列國際法譯著就作為同文館之授課教材而集中出現。據《同文館題名錄》所載,除丁韙良所譯之《萬國公法》外,當時既為早期國際法輸入中國的代表作品,又作為同文館授課教材使用的還有《星軺指掌》、《公法便覽》、《公法會通》、《中國古世公法論略》。至20世紀上半葉之法科大學與法政學堂中,外國國際法著作及教科書的翻譯更為活躍,勞麟賜所著《萬國公法要略》、今西恒太郎所著《國際法學》、高橋作衛所著《最近戰時國際公法論》、中村進午所著《戰時國際公法》及《平時國際公法》、今井嘉幸所著《中國國際法論》、橫田喜三郎所著《國際法》等的中譯本紛紛現世。一些編撰者在書中甚至連教材資料來源、適用學校、建議課時或學分都進行了專門交待。如寧協萬在其《現行國際法》中稱:本作為“著者歷年關于國際法之札記、雜錄、論著、譯述、及講演各稿,為有系統之整理,而仿德國黎斯特國際法與英國羅連士國際法之例,分作四部以成本書”。著者在“國立北京法政大學專任教授,在職八載,逐年將新得材料,加入本書,講授學子”,而其在“中國大學、朝陽大學、中央大學之講座,均以本書為講授之資”[4]1。周緯《新國際公法》中也談及,其先“擔任北大法科國際公法教授、旋南下改任中央大學國際公法教授”“,今以其兩處講義”,“出版問世”,“不負國際法學院之期望”[5]11。譚錫庠在《新編平時國際公法》中介紹,“本書原為民國十九年時之講稿徒以材料及編制未妥善故特重行增刪之”“,本書可供大學教本或參考書之用”[6]7。朱建民的《侵略問題之國際法的研究》中附有說明稱“,本叢書每冊各附導言或編后記,并各跋以討論大綱,以便各訓練班或小組討論會之應用”[7]3。張道行的“部定大學用書”《國際公法》則有更具體的指導:“本書力求深入淺出,以冀能合于初學者的應用,若采而為教科書,則以四學分至六學分為宜,每周講授兩章,適可供一年的學程之用,書中所引成案,已不算少,茍有不足,則Scott,Evans,Briggs,Dickenson的編本都可補充,實則各生如能于上述各種成案的課本中,詳研其內容,成為有用。”[8]6
由此,國際法教育的需求牽動了國際法學研究的進步:教材的編寫是教學開展的要件,也成為國際法理論延展的基礎與構成;學校刊物的創辦是國際法教研成果的展示,也是國際法學科成長的助力與印證。可以說,中國國際法教育為中國國際法學生長不可或缺之內容,其前行之步伐與國際法學之成長絲絲相扣,為近代中國國際法學體系的生成貢獻良多。(本文作者:劉暢單位:西南政法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