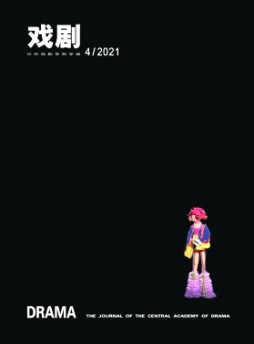戲劇化電影的特征范文
前言:我們精心挑選了數(shù)篇優(yōu)質(zhì)戲劇化電影的特征文章,供您閱讀參考。期待這些文章能為您帶來啟發(fā),助您在寫作的道路上更上一層樓。

第1篇
從大的方面講,化妝發(fā)展到今天,戲劇舞臺化妝與影視化妝在真實感、濃度、化妝品或?qū)I(yè)化妝的程度之間,已沒有很大的區(qū)別。而具體看來,它們之間又有很大的差異。例如,在大型的鏡框式舞臺上,由于距離的關(guān)系表演者已與形體、動作、服裝和表演融為一體,在后面位置的觀眾很難看到面部化妝的效果。這就需要化妝師相應(yīng)地夸張表演者的五官及面部輪廓,適當(dāng)?shù)赝怀霰硌菡叩拿嫒荨5^分強調(diào)面部底色、輪廓、眼影和眼線,在較近的觀眾來看,又會顯得太過分和外表化,影響觀眾的情緒。再如,因觀眾與舞臺的距離不同,因劇場的大小不同,其化妝程度也不同。在一些大劇院中,中間位置看來不錯的化妝在小一些的劇院中看起來顯得過分了,而在小劇場中的化妝拿到影視中又有失真的感覺。在影視化妝中,除了觀眾的距離外,媒介體系和燈光的不同也會對化妝的色彩和質(zhì)感起到一定的影響。因電影電視與舞臺制作的方法不同,所以化妝造型的表現(xiàn)也有所不同。
戲劇化妝造型是以劇本的主題思想、風(fēng)格樣式和時代背景為依據(jù),按照劇本提示的人物性格、年齡、經(jīng)歷、身份等進行設(shè)計,將其最本質(zhì)最性格化的特征表現(xiàn)在包括演員本身的形態(tài)、容貌和服飾等外部形態(tài)上。演員的容貌是觀眾的注意力集中的部位,化妝造型的任務(wù)就是圍繞演員的容貌進行的工作,通過化妝中一定的技術(shù)手段來改變和彌補某些不足,使人物的形象適合劇中的角色要求,達到可信的效果。戲劇化妝的準(zhǔn)確性除了指一般明確年齡、身份、民族、職業(yè)、個性、時代等特征的要求外,還要適應(yīng)戲劇的主題、動作、矛盾、規(guī)定情景和藝術(shù)風(fēng)格等。
戲劇舞臺化妝的主要目的是通過面部特征在演員和觀眾之間形成間離效果,對因舞臺燈光而形成的蒼白、面部光線不足的效果進行彌補,使演員保持最佳狀態(tài)。在大型的或觀眾容量較大的劇院里,由于燈光的關(guān)系,化妝的色彩和外形的重點、特征必需夸張?zhí)幚怼6谳^小的劇場里,化妝就要相應(yīng)的自然一些。另外,戲劇舞臺化妝包括寫實和抽象兩種。寫實性化妝要準(zhǔn)確地將角色化妝成現(xiàn)實生活中的人物,適用于寫實性舞臺劇。抽象性化妝則是表現(xiàn)出生活中并不存在的形象,適用于寫意的舞臺劇。在傳統(tǒng)的舞臺劇,如京劇等其化妝則一直沿用傳統(tǒng)的化妝模式,而話劇、舞劇、音樂劇等,由于演出形式的不同,其化妝也會相應(yīng)地有所變化。
電影是一種放大的藝術(shù),演員出現(xiàn)在銀幕上時往往比在生活中的真實形象要大,特別是當(dāng)整個銀幕只有一張演員的臉的時候,演員的面部的每一個細(xì)節(jié)都充分暴露在觀眾的面前。而且由于電影是膠片拍攝,膠片的感光度和清晰度很高,再加上拍攝時的燈光原因使得化妝的痕跡更容易暴露,所以電影中的化妝要細(xì)致、精密,以自然、真實為主。
第2篇
新現(xiàn)實主義在電影史范疇又稱意大利新現(xiàn)實主義,其在二戰(zhàn)后迅速發(fā)展,并掀起一波氣勢龐大、長達六年的電影新潮。新現(xiàn)實主義對世界電影的影響非常深遠,它與好萊塢電影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新現(xiàn)實主義強調(diào)樸實氣質(zhì),而不是光鮮魅力;強調(diào)表現(xiàn)普通人,而不是達官貴人;強調(diào)紀(jì)實美學(xué),而不是技術(shù)主義——這種傾向在伊朗導(dǎo)演阿斯哈·法哈蒂的影片《一次別離》中表現(xiàn)得十分明顯。小成本伊朗電影《一次別離》自2011年在第61屆柏林國際電影節(jié)輕易斬獲金熊獎后,勢如破竹般橫掃各大電影節(jié),共拿下含奧斯卡、金球獎最佳外語片等十多個全球電影重要獎項,這在當(dāng)今美國好萊塢模式大片對全球市場的覆蓋情況下是非常不易的。可以說,《一次別離》既喚起了人們對于新現(xiàn)實主義的回憶,也是導(dǎo)演法哈蒂嘗試融合伊朗本土化文化、戲劇化沖突與新現(xiàn)實主義而產(chǎn)生的一部既叫好又叫座的佳作。
一、“還我普通人”[1]與“把攝像機扛到大街上”[2]——《一次別離》對新現(xiàn)實主義題材的承襲與表現(xiàn)形式的借鑒
(一)題材與劇本立意訴求
“還我普通人”是新現(xiàn)實主義著名編劇柴伐蒂尼提出的,其主張題材表現(xiàn)普通民眾。新現(xiàn)實主義代表作品《偷自行車的人》、《溫別爾托·D》、《羅馬,不設(shè)防的城市》均是著力表現(xiàn)普通人命運的題材。與新現(xiàn)實主義的先驅(qū)一樣,《一次別離》的導(dǎo)演阿斯哈·法哈蒂也將鏡頭聚焦于伊朗人的日常生活,直面伊朗社會現(xiàn)狀,關(guān)注現(xiàn)實生活中處于道德、法律、宗教拉力中的伊朗普通百姓。影片的切入點極小——從納德與西敏的分居為切入,但這個小切入點卻深刻地扎進了伊朗社會的肌理脈絡(luò)之中:一次意外事件后各種矛盾接踵產(chǎn)生,逐步深入最終走向一個不可逆轉(zhuǎn)的別離結(jié)局。劇中兩個普通的伊朗家庭在法律與道德面前的矛盾展現(xiàn)了伊朗錯綜復(fù)雜的社會現(xiàn)實,也揭示了一次分離:伊朗社會凝聚力的分離。
導(dǎo)演用旁觀者視角貼近而不動聲色地記錄事件,同時洞悉人與人之間復(fù)雜微妙的關(guān)系,把大量日常生活的要素和情境升華為一個跌宕起伏的故事,對人性的刻畫極其深刻,在原生態(tài)的生活展現(xiàn)過程中反映了伊朗人真實而又頗為無奈的生活,質(zhì)樸真誠地強調(diào)了新現(xiàn)實主義人文精神的延續(xù)。
(二)表現(xiàn)形式
在拍攝手法上,新現(xiàn)實主義還提倡“把攝像機扛到大街上”的創(chuàng)作口號——對拍攝手法與表現(xiàn)手段方面提出了一定的紀(jì)實要求。新現(xiàn)實主義很少布景拍攝,強調(diào)手持?jǐn)z像;在光線處理上,傾向于采用自然光。《一次別離》也繼承了新現(xiàn)實主義這種典型的攝制方式,全片長達兩小時,多是利用自然光線手持跟拍,如一部不加修飾的記錄片;大量的主觀鏡頭干凈而克制地將觀眾帶入情境之中。無論室內(nèi)室外都狹仄,密閉的空間內(nèi)人們心事重重;走出室外,映入眼簾的是伊朗城市的車水馬龍,又讓人覺得心緒紛亂。鏡頭之下,伊朗的風(fēng)土民情雖然遙遠而陌生,但觀眾對這些城市景象卻非常熟悉,因為就如每天環(huán)繞在自己身旁的生活一隅。
在藝術(shù)表現(xiàn)手段上,《一次別離》也絲毫不給觀眾有出戲疏離的機會。注重運用長鏡頭,以連貫的拍攝獲取真實效果一直是新現(xiàn)實主義紀(jì)實美學(xué)的一個重要特征。“新現(xiàn)實主義電影采用的長鏡頭,是用連續(xù)攝影法拍攝的景深鏡頭,強調(diào)的是鏡頭內(nèi)部的空間調(diào)度和場面調(diào)度,從而在一個統(tǒng)一的時空中相對完整的展現(xiàn)動作和事件。這樣,長鏡頭對現(xiàn)實的表現(xiàn)就具有空間的完整性、時間的連續(xù)性和影像的客觀性。” [3] 而“長鏡頭紀(jì)實美學(xué)”來源于安德烈·巴贊[4],其運用的意義首先在于真實感,不作分切的一次性連續(xù)拍攝,使銀幕畫面人物活動的影像完整性與被表現(xiàn)的客觀現(xiàn)實達到高度統(tǒng)一。例如,《偷自行車的人》中大部分段落都是用長鏡頭描述的, 如失業(yè)者圍著政府職員求職, 里西到典當(dāng)鋪贖回自行車. 里西和兒子在舊貨市場尋找被偷的自行車; 里西偷別人的自行車時被發(fā)現(xiàn)等,這些段落都沒有鏡頭的切換, 保持了人物行動和事件的連續(xù)和相對完整。另外, 長鏡頭保留了現(xiàn)實本身的多義性。蒙太奇強制觀眾跟著導(dǎo)演的意圖去被動地理解影片, 長鏡頭卻讓觀眾直接參與銀幕中的現(xiàn)實,由觀眾自己去作判斷解釋。
《一次別離》中,長鏡頭使用突出表現(xiàn)在影片的開頭與結(jié)尾:電影開篇記錄式的拍攝手法,近四分鐘一鏡到底、甚至帶有些輕微晃動的長鏡頭,直截了當(dāng)?shù)刈屛髅艉图{德這對夫妻對簿公堂,上演了一出你來我往的家庭紛爭,有著很強的感染力。觀眾被置于法官的視野位置去審視這場糾紛的是與非。難以判斷誰是誰非的法官,最后令其簽字回家和解,不予離婚,畫面中只留下兩張空椅。此時,觀眾已被這個連續(xù)的長鏡頭帶入故事情境之中,旋即被卷入環(huán)環(huán)相扣的劇情里。而影片以一個長鏡頭開始,也是以一個長鏡頭結(jié)尾,場景仍舊是法院,不同的是二人已在等待離婚后女兒的抉擇。一氣呵成的鏡頭冷靜客觀地對著這個長廊,人來人往中,納德和西敏相向而坐,二人中間以一扇破裂的玻璃門作為分界,兩人各占據(jù)畫面的一角,茫然而又無言以對,等待女兒的決定,等著著別離。玻璃上的裂痕仿佛就是納德和西敏這個家庭之間,也是整個伊朗社會之間的裂痕與隔閡。這時,長鏡頭帶來的強烈沖擊力審問觀眾,如果是你我,當(dāng)如何選擇。這兩處首尾呼應(yīng)的長鏡頭耐人尋味,猶如“神來之筆”:相同的地點、不同的命運走向,掃視著劇中主人公納德與西敏對于生活的無奈,也調(diào)動了觀眾融入劇情的參與感,同時也完美地展現(xiàn)了導(dǎo)演對于新現(xiàn)實主義電影紀(jì)實美學(xué)的推崇。
而開放式結(jié)局也是新現(xiàn)實主義電影藝術(shù)表現(xiàn)手段的一個不可磨滅的特征。柴伐蒂尼提出“不給觀眾提供解決問題的答案” [5] ——對比《偷自行車的人》影片結(jié)尾,里西與兒子一起走,沒有臺詞,沒有音樂,僅有周圍的環(huán)境聲的開放式結(jié)局,《一次別離》則通篇都只有真實的環(huán)境音,僅在影片結(jié)尾突然插入了兩段鋼琴聲,緩慢而沉重的和弦一鳴驚人。這悲愴傷感的音樂——也是本片唯一的配樂,猶如沉默中情感的噴發(fā),讓觀眾陷入一種沉重的、難以言表的延續(xù)性思考,且直至片尾音樂結(jié)束,觀眾也沒有等到女兒特梅的最終選擇。音樂聲中,極富深意的長鏡頭已完成了影片開放式結(jié)局,這種戛然而止的開放式結(jié)局處理方式甚至比《偷自行車的人》顯得更甚一籌。
二、融合伊朗宗教文化和經(jīng)典的戲劇化策略進行敘事表達——《一次別離》是對新現(xiàn)實主義的伊朗本土化詮釋
就題材、主題、人物形象塑造、人文精神、藝術(shù)手法與表現(xiàn)手段運用上而言,《一次別離》無疑是新現(xiàn)實主義電影的一個完美樣本。但羅伯托·羅西里尼[6]說過:“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新現(xiàn)實主義。”[7]伊朗作為一個政教合一的國家,當(dāng)局嚴(yán)苛的審查制度使電影題材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宗教文化與政治氛圍一直縈繞著伊朗電影,也因此伊朗電影在國際影壇上存在著一種有別于西方電影的神秘性與特殊性。
當(dāng)伊朗導(dǎo)演阿巴斯·基阿羅斯塔米執(zhí)導(dǎo)的影片《櫻桃的滋味》1997年在戛納摘下金棕櫚獎,電影界才發(fā)現(xiàn)新現(xiàn)實主義在伊朗仍興盛著。事實上,伊朗三大導(dǎo)演除了阿巴斯之外,莫森·瑪克瑪爾巴夫、賈法·帕納西的電影風(fēng)格均帶有深刻的新現(xiàn)實主義美學(xué)印記。幾代伊朗導(dǎo)演都將新現(xiàn)實主義美學(xué)之根植于伊朗傳統(tǒng)文化的土壤之中,表現(xiàn)出“對本土現(xiàn)實、文化和本土體驗的殷切關(guān)懷”。[8]但是伊朗過去的新現(xiàn)實主義電影非戲劇化的敘事雖含有詩意哲學(xué),但劇情張力不強,電影表達只觸及了伊朗社會生活的現(xiàn)實表面,主題不夠深刻。
“文化離開誠實而強有力的故事便無從發(fā)展。”[9]作為第三代伊朗導(dǎo)演的阿斯哈·法哈蒂深深意識到了這一點,他在恪守新現(xiàn)實主義的精神內(nèi)核原則外,對伊朗本土化具有現(xiàn)實意義的多重問題(伊朗人民的信仰、階級、感情、法律、倫理、教育)進行了思考,交織了經(jīng)典的戲劇化沖突敘事策略:嚴(yán)格按照開端—發(fā)展——結(jié)局的邏輯線索來結(jié)構(gòu)故事,將矛盾沖突與戲劇懸念埋入敘事,追求情節(jié)結(jié)構(gòu)上的環(huán)環(huán)相扣。
經(jīng)典的戲劇化沖突敘事策略還是《別離》好看的一個重要的因素,影片的敘事主線基本上是通過懸念來牽引的。首先“納德和西敏的婚姻最終會是什么結(jié)局,離婚還是和好?”是貫穿影片始終的一個懸念。而結(jié)尾又留下了“女兒會選擇誰?”的懸念待人深思。另外一條敘事線——納德與女傭瑞茨的糾葛段落中,也是采用了制造懸念的敘事手法,“誰偷了錢?他聽到?jīng)]有?她有沒有撒謊?他們會不會和解?他們會不會拿錢?”一個個懸念在引導(dǎo)著敘事迂回地深入,直至結(jié)局。如果說從原本的故事角度來看,《別離》的故事并不討好大多數(shù)觀眾,它只講述了一個簡單的家庭和社會悲劇,那么是導(dǎo)演法哈蒂通過嫻熟的經(jīng)典敘事手法使內(nèi)容具有了觀賞性。
“沖突實質(zhì)上體現(xiàn)了電影中人物的想法、行動與社會的一種對抗性關(guān)系。”[10] 縱觀全劇,多重矛盾關(guān)系或隱或顯,或大或小,構(gòu)成了形態(tài)各異的沖突:社會階層之間的沖突——納德一家所代表的是中產(chǎn)階層,有房有車有穩(wěn)定的工作;而瑞茨代表的是伊朗下層的勞動人民,家庭負(fù)債,懷孕仍要外出工作,丈夫失業(yè)。瑞茨的意外流產(chǎn),使兩個家庭彼此間產(chǎn)生強烈的對立,階層立場不同又造成和解的困難。隨之劇情承載了第二個沖突:伊朗宗教與人性的矛盾,影片在很多情節(jié)涉及到:如瑞茨在照顧納德父親時所猶豫的宗教禁忌、家庭教師在對著《古蘭經(jīng)》作偽證后又復(fù)而到法院改口供的前后變化以及最后雙方和解過程中瑞茨對教義會懲戒女兒的疑慮……暗含的強烈沖突便是宗教與人性的矛盾,在伊朗這個國度,現(xiàn)代化過程中對于人的束縛與人對束縛的掙扎都是不可回避的事實。沖突使《一次別離》的敘事形成特有的張力,它不僅激發(fā)了觀眾的觀賞興致,還在沖突中彰顯了劇中人物的個性,并生發(fā)出更富意味的敘事隱喻。
第3篇
提及喜劇電影表演的戲劇性,不乏又有人會從電影表演的"去戲劇化〃出發(fā)而提出質(zhì)疑。其實業(yè)界早已有學(xué)者對"去戲劇化"進行了理論上的反思。"去戲劇化〃并不等于"去戲劇性”所謂"戲劇性〃就是指:"在假定性的情境中展開直觀的動作,而這樣的情境又能產(chǎn)生懸念、導(dǎo)致沖突;懸念吸引、誘導(dǎo)著觀眾,使他們通過因果相承的動作洞察到人物性格和人物關(guān)系的本質(zhì)。"Q)“去戲劇化〃的偏頗在于:"摒棄戲劇性,弱化情節(jié)性,忽略人物塑造和演員表演”以至于“一部電影最重要的部分一人、情節(jié)、戲劇性、矛盾沖突,以及他們折射出的社會意義,皆因’去戲劇化’而被拋棄掉了。"⑷"被拋棄掉〃的恰恰是喜劇電影所需要強化的,甚至超乎于其他類型電影的需要,不能想象一部喜劇電影如果缺失了"情節(jié)性〃"人物塑造〃和"演員表演〃還有什么喜劇性可言。誠然,電影在結(jié)構(gòu)形態(tài)方面不同于戲劇,它具有與戲劇藝術(shù)截然不同的時空特性,因此,那種虛假的、過火的、脫離真實的、夸張的舞臺化表演是電影藝術(shù)應(yīng)該排斥的,同時更是話劇藝術(shù)所排斥的。電影藝術(shù)和戲劇藝術(shù)在克服虛假的舞臺化傾向時,都不排斥戲劇性。
眾所周知,“一部喜劇作品往往通過選材與巧妙的編排來達到令人賞心悅目的藝術(shù)效果。劇中人物和他們的挫折困境引起的不是憂慮而是含笑會意,觀眾確信不會有大難來臨,劇情往往是以主人公如愿以償為結(jié)局"。"選材”"巧妙編排〃"挫折困境〃都是體現(xiàn)出喜劇作品戲劇性情境設(shè)置的獨特性,這包含了具體的時空環(huán)境、特定的事件以及獨特的人物關(guān)系等戲劇性的基本要素。
例如在《泰冏》和《心花路放》兩部影片中,都以小人物為主角,以公路片的類型模式展開敘事,人物在基于"尋找"的最高任務(wù)中展開一段曲折的旅程,這樣的設(shè)置很好地將封閉式情境和開放式情境結(jié)合在一起。這種封閉式情境主要在于人物的心理空間,旅程在異鄉(xiāng)展開,貌似風(fēng)光旖旎、景點頗多,但對于劇中人物來說卻是舉目無親、交流不暢、孤立無援,類似一個孤島,是一個陌生的的環(huán)境,心理空間是封閉的。這種封閉的優(yōu)點在于敘事更加集中,遵循著"開端一發(fā)展一一結(jié)局"的封閉式敘事模式規(guī)律,《泰冏》中就是圍繞著獲取股東周先生的授權(quán)這一事件展開的,如《心花路放》則是圍繞著"療傷""獵艷"展開的;人物關(guān)系也能夠僅僅圍繞著同在旅途中的角色之間展開,充分構(gòu)建角色之間的沖突,如《泰冏》主要構(gòu)建了徐朗一一王寶、徐朗——高博、王寶——高博這一組三角關(guān)系之間的沖突;同時,人物心理空間的封閉性更集中地展現(xiàn)人物內(nèi)部自身的性格沖突,如《泰冏》中徐朗始終徘徊在事業(yè)與家庭之間的選擇,游離在面對競爭對手高博時的矛盾對立和善良友情之中。而開放式情境主要體現(xiàn)在戲劇情境的流動性,旅途中每到一處新的地點,就產(chǎn)生一個新的戲劇化的情境,繼而孕育出一組新的人物關(guān)系,產(chǎn)生新的矛盾沖突,構(gòu)成戲劇情境的多變流動,這給演員的創(chuàng)作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在豐富多變的情境中,為角色充分展現(xiàn)性格中的復(fù)雜因素提供了必要的條件。如《心花路放》中,郝義(徐崢飾)和耿浩(黃渤飾)從城市出發(fā),歷經(jīng)湖南天門山的鄉(xiāng)村大舞臺和夜市邂逅了"阿凡達女孩"、芙蓉小鎮(zhèn)的美發(fā)廳碰上了"殺馬特女孩"、在前往香格里拉的公路上幫助了"美艷白領(lǐng)"、在大理遭遇了"小姐們"與"黑幫老大",這一系列的環(huán)境地點的變換與人物關(guān)系的組建,構(gòu)成了影片流動的喜劇情境,極富戲劇性。
"戲劇思維和電影思維中的沖突意識,首先意味著設(shè)置戲劇情境。"富有戲劇性的具體情境能夠迫使人物采取積極主動的行動,進而充分地展現(xiàn)自己的性格。這種戲劇情境的封閉與開放構(gòu)成了影片中的情境沖突,產(chǎn)生了一種戲劇性的對于曰常生活提煉的非常態(tài),容納了事件發(fā)生的一切偶然性和必然性。"偶然性是構(gòu)成戲劇性的必要因素之一。”m在喜劇中更是占據(jù)著極為重要的地位。在《泰冏》中,徐朗與王寶偶然在去往泰國的飛機上邂逅、一個偶然丟了護照、一個偶然忘帶錢包、兩人偶然闖入了倒賣文物的地下市場……全劇的動作正是由一系列偶然事件開始并串聯(lián)的,在偶然性的事件中,產(chǎn)生了誤會、巧合,強烈的喜劇性正是源于這些接連不斷的誤會和巧合之中。把人物置于一個偶然的情境之中,就像放在一個放大鏡下,讓他們的性格充分暴露出來,沒有偶然性事件,這出喜劇就不會存在了。然而,如果演員僅僅注意把握情境之中的偶然性因素,而忽視了產(chǎn)生偶然性的必然的根源,只能使自己的表演浮于極力表現(xiàn)表面滑稽,著重于表現(xiàn)動作中的誤會、巧合,并不能使自己的表演上升為一種機智的幽默。?例如《泰冏》中徐朗與高博之間的利益爭奪是一種必然因素,由于高博的緊追不舍,導(dǎo)致了徐朗利用與王寶之間的各種偶然事件來擺脫高博的追蹤。任何一種偶然都是一種必然,必然性的根源就蘊含在復(fù)雜而鮮明的人物性格之中。只有把握住角色的性格邏輯,通過人物自身性格的展現(xiàn)和人物之間性格的沖突,才能將戲劇性的喜劇情境呈現(xiàn)出來。
徐崢的喜劇表演很善于把握角色的性格邏輯,并且把握住"意志沖突〃和"性格沖突〃進行喜劇人物的刻畫,他大多數(shù)喜劇作品都是由這兩點交互產(chǎn)生的。"自覺意志使人們?yōu)榱藢崿F(xiàn)既定目的而采取行動,而獨特的行動方式卻是由個人性格中的諸種復(fù)雜因素決定的。"?其中意志沖突構(gòu)成了行動的起點,性格的沖突構(gòu)成了其表演的喜劇性。《泰冏》中,徐崢飾演的徐朗是一個成功的商業(yè)人士,嚴(yán)肅認(rèn)真,擁有極強的事業(yè)心卻忽視了家庭情感的經(jīng)營,最終導(dǎo)致了事業(yè)上和家庭情感上的諸多瓶頸,影片開始就通過他的表演處理展現(xiàn)出了角色所處的矛盾境地:向妻子介紹實驗成功的"油霸〃時,表現(xiàn)得十分自信,語氣堅定;而當(dāng)妻子提出離婚時,他瞬間處于矛盾境地,充滿了無奈和對經(jīng)營家庭失敗的沮喪。相較于另外一個人物,由黃渤飾演的高博,整個人物狀態(tài)呈現(xiàn)出一種病態(tài)的偏執(zhí),為了追求利益,他棄臨盆的老婆于不顧,與當(dāng)年的好友徐朗反目,這兩個人物之間屬于意志的沖突。影片中由王寶強飾演的人物王寶,樂觀天真,表面上看是一個草根,在身份上似乎成為精英人士徐朗的對立面,然而這兩個人物之間的沖突并不僅僅是社會身份、地位的沖突,更主要的是人物之間性格的沖突。整部影片的喜劇性就是從三個人物之間意志沖突與性格沖突的展開過程中呈現(xiàn)出來的。黑格爾說"若干人在一起通過性格和目的的矛盾,彼此發(fā)生一定的關(guān)系,正是這種關(guān)系形成了他們的戲劇性存在的基礎(chǔ)。"
從微電影《_部佳作的誕生》開始,徐崢就嘗試以導(dǎo)演身份介入喜劇電影創(chuàng)作,終于自編自導(dǎo)自演了《泰冏》,擔(dān)任《摩登年代》的監(jiān)制,筆者將這看作是演員尋求作為演員的個性化表達的一種途徑,或許是化被動創(chuàng)作為主動創(chuàng)作的一種手段。在《泰冏》中,由于他擔(dān)任編劇、導(dǎo)演和主演,也使其成為這部影片的真正作者。這種身份,可以給徐崢的表演創(chuàng)作帶來極大的空間,獲得了作為演員最大的主動權(quán)。作為影片的作者,他可以根據(jù)自身條件"量身定制〃角色,從而最大限度地發(fā)揮優(yōu)點和長處,一定程度上最大可能性地將演員個人魅力與角色的魅力相互結(jié)合起來,也正因如此,能夠在影片中充分展現(xiàn)演員的魅力,甚至影響影片整體表演格調(diào)。
基于身份的轉(zhuǎn)型和知名度、影響力的提升,徐崢能夠在他所主演的影片中使自己的喜劇表演方法和理念逐步滲透,形成了他獨具魅力的喜劇表演特征。有著專業(yè)戲劇院校學(xué)習(xí)背景的徐崢畢業(yè)之后在上海話劇藝術(shù)中心擔(dān)任演員,成功出演過多部話劇作品。舞臺表演創(chuàng)作并沒有束縛他在銀幕前的人物塑造,也沒有給他的表演帶來所謂的"戲劇化〃的虛假、過火;相反,豐富的舞臺表演經(jīng)驗賦予徐崢扎實而有深度的表演創(chuàng)作技法。他所塑造的喜劇人物形象看似平靜不張揚,舉手投足間透露著一股海派小資情調(diào)的幽默元素,將人物的狡黠與機智通過對人物性格的多層次挖掘和把握自然流露,講究細(xì)膩的情感體驗和情感爆發(fā)的張力,充滿了表演藝術(shù)的技巧,飽含了戲劇性的因素。
這些"徐氏喜劇表演〃特征在其自編自導(dǎo)自演的《泰冏》中發(fā)揮到了極致,具體體現(xiàn)在以下兩個方面:
—是人物形象的凝練。徐朗這個角色延續(xù)了徐崢?biāo)茉斓母鞣N喜劇人物形象共有特點:從職業(yè)上來說,屬于都市白領(lǐng)階層,看似光鮮,實則卻陷于事業(yè)發(fā)展瓶頸、家庭情感失敗、昔日好友的反目三重困境,并不屬于完美的精英群體,可以說是生活在巨大壓力之下的"偽中產(chǎn)"。從人物造型來看,始終保持著身穿西服的光頭形象,圓圓的腦袋配合略顯肥嘟嘟的臉,顯得有些滑稽和不成熟,與成功白領(lǐng)精英的理想形象有比較大的反差。同時,隨著影片中徐朗和王寶經(jīng)歷—個又一個困境之后,在人物造型上又給人物增加了破敗感和逃亡感,臟兮兮的衣服、幾天沒洗的臉、淤青的眼眶以及細(xì)小的傷口……這些造型上的處理,達到了對角色的"丑角化〃塑造,喜劇電影中"每一個角色都會_定程度地受到扭曲,這種變形_定程度上丑角化了現(xiàn)實生活中的人物”,(12)使觀眾產(chǎn)生了俯視角色的優(yōu)越感,從而產(chǎn)生了含義不同的笑聲。從語言表達上來看,略帶方言的口音帶有地域性的特點,加之較快的語言節(jié)奏,讓人直接聯(lián)想到大都市的生活節(jié)奏和壓力。這些在人物形象設(shè)定和表演處理,無不遵循著喜劇電影表演的創(chuàng)作規(guī)律,又體現(xiàn)著屬于徐崢本人的自我特點。
二是在處理演員與角色的矛盾統(tǒng)_的關(guān)系時,徐崢的表演創(chuàng)作選擇了讓角色向演員靠攏,讓角色具備演員的氣質(zhì)、個性魅力,強化運用演員本人的特點。這種"本色化〃的表演理念,表面看似只做到了"從自我出發(fā)”,沒有"通向角色”,但卻使徐崢將更多塑造的功力運用到挖掘和體現(xiàn)不同角色的性格魅力上,沒有局限于"自我"。原因有兩點:在當(dāng)下"明星制"的電影生產(chǎn)過程中,很多角色就是為明星量身定制的,在設(shè)定角色的類型的時候,就預(yù)先賦予了角色屬于演員本人的諸多性格特征,角色即是演員本人的類型,這是其一;其二,每個角色所處的情境不同、糾葛的人物關(guān)系不同,徐崢把握住充分展現(xiàn)性格中的復(fù)雜因素的情境條件,把人物放在豐富多變的情境之中去動作,從而塑造了一個又一個豐富多彩的、層次鮮明的角色性格。舉個例子來說,《愛情呼叫轉(zhuǎn)移》和《泰冏》中,徐崢飾演的角色雖然都叫"徐朗"但是此"徐朗"非彼"徐朗"。《愛情呼叫轉(zhuǎn)移》中的徐朗是一個好男人,經(jīng)歷過"七年之癢〃后,與發(fā)妻離婚,卻偶然地得到了一部具有神奇力量的手機,并與12個不同星座的女人分別談了一次戀愛。而《泰冏》之中的徐朗,為了實現(xiàn)自己的事業(yè)夢想幾乎耗盡了所有的心血和精力,承受著事業(yè)、家庭、友情和尋找自我本真的壓力,這也正是當(dāng)下很多中年人都會遇到的問題,這個徐朗在經(jīng)歷了一系列的冏事之后,逐漸認(rèn)清了人生的真諦,回歸了本真的自我。雖然這兩個角色都有"徐朗〃的名字,或者說都打上了"徐崢〃的標(biāo)簽,但是演員把握住了"人物所處的環(huán)境應(yīng)該是獨特的,人物的經(jīng)歷應(yīng)該是獨特的,人物性格應(yīng)該是獨特的,人物的遭遇、命運也應(yīng)該是獨特的"。由此產(chǎn)生了具體、個別、獨特的藝術(shù)形象,避免了千人一面的雷同。
徐崢演的喜劇角色很多,對此他說:"做演員就是這個樣子的,如果你成功的塑造過某一個形象,那么就會有許多相類似的角色來找你。我希望在下一部戲里面,不動聲色,不用表情,也能把我的思想表達出來。不過如果沒有這樣的角色,我還是會開心地把我所扮演的每一個角色演好的。"這段話從一個側(cè)面反映出當(dāng)下電影產(chǎn)業(yè)對于演員的擇取存在一種類型化的趨向,"充分發(fā)揮演員自身的獨特魅力并將其和諧地注入角色則成為創(chuàng)作的一個關(guān)鍵"。這正是類型電影對于類型化表演的訴求體現(xiàn)。從另一方面來說,針對相同類型的角色,從深度和精確度上挖掘這個表演的類型,把握演員表演成功的規(guī)律,為類型電影培養(yǎng)能夠符合創(chuàng)作規(guī)律的演員,不失為對當(dāng)下喜劇電影類型、電影表演美學(xué)觀念發(fā)展以及電影演員格局多層面構(gòu)建的有益之舉。"根據(jù)’自我認(rèn)定’設(shè)計’自我動作’,形成一種獨特的再體現(xiàn)和鮮明的性格化,并以個性化和生命化地通過表演詮釋真實意圖,表演也就有著一種個性表演魅力的美學(xué)符號性質(zhì)。"類型但不雷同,在類型中尋找個性化的差異化表達,正是對于類型化表演的要求。
徐崢對"什么是喜劇〃有特別深入的思考:"喜劇不是簡單的搞笑和幽默能夠概括的,你會發(fā)現(xiàn)人生就是一個悲喜劇。偉大的喜劇里面應(yīng)該摻雜著悲劇,像卓別林的電影。你想想他的喜劇其實是一個悲劇,但是你在看的時候會不停地笑,可是你從電影院出來的時候,你特別難過。這才是偉大的喜劇。喜劇一定要有感動人的東西。"徐崢對于喜劇創(chuàng)作的理解充滿著戲劇性的思辨,體現(xiàn)著一個演員的情懷以及人文關(guān)懷。《愛情呼叫轉(zhuǎn)移》中的徐朗對于愛情和婚姻的重新認(rèn)知和理解,《摩登年代》中的歐大衛(wèi)從一個靠著魔術(shù)計量行騙于江湖的"小丑"到受"父女"之間充滿魔力的愛的感召而回歸良知,《泰囧》中的徐朗放棄既得利益重回家庭的溫情港灣,《心花路放》中視情感為兒戲的浪子郝義回歸真摯的愛情……這些人物無不通過徐崢的表演體現(xiàn)出一種人物在喜劇外表下的內(nèi)在的戲劇性,即內(nèi)心的沖突、意志的轉(zhuǎn)變、情感的波瀾。
"喜劇電影的情節(jié)多夸張,看似與現(xiàn)實主義美學(xué)格格不入,但它并非脫離現(xiàn)實的游戲。相反,喜劇電影與現(xiàn)實的關(guān)聯(lián)性是它極其重要的屬性。"通過喜劇的形式來反映社會和人生,揭示時代背景下人的生存境況,就是這種現(xiàn)實的關(guān)聯(lián)性,而這一切都要從演員具體的表演創(chuàng)作中透露出來,在起伏跌宕的外部行動中展現(xiàn)喜劇性,更要在人物內(nèi)在把握由于思想的沖突、感情的波瀾而造成的戲劇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