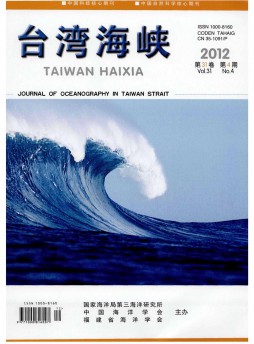臺(tái)灣新世代本土詩(shī)人的想象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zhǔn)備了臺(tái)灣新世代本土詩(shī)人的想象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diǎn)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xiě)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廣東社會(huì)科學(xué)雜志》2015年第四期
在傳統(tǒng)的研究視野里,“代”或“世代”往往指涉的只是人的生理、自然屬性。無(wú)論是“前行代”,還是“新生代”,都是由特定年齡層的人構(gòu)成的。不過(guò),“代”或“世代”又不僅僅是一個(gè)時(shí)間性的范疇,也是一個(gè)社會(huì)文化性的范疇。正因如此,在現(xiàn)代的研究視野里,研究者越來(lái)越開(kāi)始重視“代”或“世代”的社會(huì)文化屬性。由此看來(lái),現(xiàn)代性意義的“代”或“世代”范疇,總的來(lái)說(shuō)是現(xiàn)代社會(huì)發(fā)展的生成物,或者說(shuō),它作為一個(gè)“現(xiàn)代性”的范疇,是伴隨著人類(lèi)社會(huì)的現(xiàn)代化的進(jìn)程而生成的。現(xiàn)代性以及作為其主要表征的現(xiàn)代化,使“代”或“世代”的學(xué)術(shù)價(jià)值和實(shí)踐意義極大地突顯出來(lái)。
一、“世代”亞群體:本土與外省
“代”或“世代”成為一個(gè)現(xiàn)代性的問(wèn)題是從20世紀(jì)初、中期年輕世代的崛起所引起的不同的世代的文化沖突開(kāi)始的。在這個(gè)時(shí)期,卡爾•曼海姆、羅貝爾•埃斯卡皮、瑪格麗特•米德等研究者們發(fā)現(xiàn),不同的世代的文化對(duì)立、沖突已經(jīng)滲透到社會(huì)的政治、經(jīng)濟(jì)、道德等各個(gè)層次。正因如此,卡爾•曼海姆、羅貝爾•埃斯卡皮、瑪格麗特•米德等研究者在承認(rèn)“代”或“世代”是由一定年齡層的人組成的前提下,又都認(rèn)為年齡等自然屬性不是“代”或“世代”的本質(zhì)屬性,“代”或“世代”的本質(zhì)屬性是社會(huì)文化屬性。因?yàn)椋挥性诨鞠嗤纳鐣?huì)文化環(huán)境的影響下,處于同一年齡層的人才會(huì)生成基本相同的政治取向、價(jià)值理念、思維方式、情感指向和生活習(xí)慣。緣此,同時(shí)賦予“代”或“世代”以生物學(xué)和社會(huì)學(xué)意義,以特定的年代和具有重要象征意義的社會(huì)的結(jié)構(gòu)性變動(dòng)和歷史、文化事件來(lái)區(qū)別和定義“代”或“世代”的方法被卡爾•曼海姆、羅貝爾•埃斯卡皮等、瑪格麗特•米德等研究者廣為援用。20世紀(jì)80年代,隨著“世界政治格局的變化、臺(tái)灣內(nèi)部的變革、兩岸關(guān)系的緩和以及資訊化都市社會(huì)的形成,必然使整個(gè)社會(huì)文化環(huán)境和文化流向也隨之發(fā)生根大的改變。”①社會(huì)結(jié)構(gòu)的轉(zhuǎn)型和文化的急劇變遷,使得臺(tái)灣不同的世代的文化對(duì)立、沖突日趨尖銳而又激烈。時(shí)代的需要如長(zhǎng)江后浪推前浪一樣地推出了新的世代。他們帶著新的時(shí)代需要與個(gè)體需要,以新的政治取向、價(jià)值理念、思維方式和情感態(tài)度審視一個(gè)生理代際和文化代際的關(guān)系出現(xiàn)“裂變”的從未有過(guò)的新世界。而首先順應(yīng)這種新陳代謝的歷史發(fā)展潮流要求的正是20世紀(jì)80年代登上文壇的臺(tái)灣新世代作家林燿德、黃凡、簡(jiǎn)政珍等人。從1986年開(kāi)始,他們相繼推出了《一九四九以后———臺(tái)灣新世代詩(shī)人初探》、《不安海域———臺(tái)灣新世代詩(shī)人新探》、《新世代小說(shuō)大系》、《臺(tái)灣新世代詩(shī)人大系》等為臺(tái)灣新世代文學(xué)吶喊和正名的著作。在這些著作中,他們都強(qiáng)調(diào)了新世代和新世代作家超越前行代和前行代作家群體的獨(dú)特的“代”的文化特征:“這一代的詩(shī)人比上一代更具慧眼,而是應(yīng)和時(shí)代遞嬗,他們有一顆更具挑戰(zhàn)的心。”②因而,他們天經(jīng)地義地認(rèn)為新世代作家擁有“書(shū)寫(xiě)當(dāng)代,也創(chuàng)造當(dāng)代”的權(quán)力。③他們宣稱(chēng):“我們有權(quán)利擁抱視野所及的一切、化育養(yǎng)成新天新地,也有權(quán)利粉碎人間一切斯文掃地的迷思與龜裂崩頹的偶像。”
這種急于通過(guò)顛覆前行代和前行代作家群體的權(quán)威來(lái)確立、彰顯自己的世代的存在的策略與方式,既是林燿德、黃凡、簡(jiǎn)政珍等新世代作家在主體意識(shí)上的自我覺(jué)醒的表征,也是一種超越前世代意識(shí)的先鋒精神的體現(xiàn)。而從某種程度上說(shuō),只有具備了這種先鋒精神,林燿德、黃凡、簡(jiǎn)政珍等新世代作家的現(xiàn)代性意識(shí)才能得以確立。雖然他們有時(shí)在以“斷裂”的姿態(tài)反叛、顛覆既有的思想觀念、思維模式和表達(dá)方式時(shí)顯得有些矯枉過(guò)正,但是,不可否認(rèn)的是,沒(méi)有這種反叛和顛覆,作為創(chuàng)作主體的林燿德、黃凡、簡(jiǎn)政珍等新世代作家的主體精神的獨(dú)立和自由就不可能獲得充分實(shí)現(xiàn),新世代和新世代作家的命名的合理性與現(xiàn)代性意義就不能獲得如此大的社會(huì)關(guān)注度,20世紀(jì)末、21世紀(jì)初的臺(tái)灣文學(xué)就不會(huì)變得如此新穎、奇特、多姿多彩。隨著臺(tái)灣與大陸社會(huì)快速的發(fā)展,新世代與前生代的矛盾與對(duì)立也日趨尖銳、激烈。無(wú)論在臺(tái)灣還是在大陸,對(duì)代際關(guān)系較為關(guān)注的研究者都能非常明顯地感受到臺(tái)灣新世代文學(xué)的強(qiáng)大滲透力和沖擊力,因而,一些眼光敏銳的研究者也加入到對(duì)臺(tái)灣新世代文學(xué)進(jìn)行界定與闡釋的隊(duì)伍中來(lái),發(fā)表了一些頗為扎實(shí)的研究成果。其中,大陸學(xué)者朱雙一的《近二十年臺(tái)灣文學(xué)流脈———“戰(zhàn)后新世代”文學(xué)論》、王金城的《臺(tái)灣新世代詩(shī)歌研究》)、臺(tái)灣學(xué)者孟樊的《臺(tái)灣中生代詩(shī)人論》等論著是較為突出的代表。這些論著與上述的林燿德、黃凡、簡(jiǎn)政珍等的論著雖然在研究理念、思維、方法上不完全相同,但都呈現(xiàn)出了一些共同的研究態(tài)勢(shì)與特色。
首先,這些論著在對(duì)臺(tái)灣新世代文學(xué)的界定時(shí)都注意到了它的自然屬性。大致而言,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兩種以年齡作為劃分新世代的標(biāo)準(zhǔn):第一種以林耀德、朱雙一、孟樊等的界定為代表。他們所謂的“新世代作家”的起點(diǎn)線均為1945年至1949年,終點(diǎn)線均為1969年。第二種以王金城的界定為代表。他以1945年至1949年間出生者作為“新世代作家”的彈性起點(diǎn)線,以1979年出生者作為“新世代作家”的下限線。相對(duì)而言,我們更為認(rèn)同王金城的界定標(biāo)準(zhǔn)。這是因?yàn)椋魏卫碚撋系拿徒缍偸遣豢杀苊獾販笥谖膶W(xué)創(chuàng)作,總是在對(duì)過(guò)往的文學(xué)事實(shí)進(jìn)行歸納、概括、總結(jié)的同時(shí)忽視了正在演進(jìn)的豐富而又復(fù)雜的文學(xué)現(xiàn)象。而王金城的界定標(biāo)準(zhǔn)的可貴之處在于,它充分地考慮到了這一概念的流動(dòng)性、后延性的重要特征,將20世紀(jì)末極為活躍的1970年至1979年出生的臺(tái)灣詩(shī)人納入到了新世代詩(shī)人的范圍。由此,相對(duì)而言,他的界定標(biāo)準(zhǔn)就具有更強(qiáng)的有效性和針對(duì)性。不過(guò),我們也必須認(rèn)識(shí)到,盡管這些研究者對(duì)臺(tái)灣新世代作家的時(shí)間范圍的限定存在著一定的差異,然而,他們關(guān)于臺(tái)灣新世代作家的生成的語(yǔ)境都沒(méi)有逾越“二次大戰(zhàn)以后”這個(gè)起點(diǎn)和20世紀(jì)80年代這個(gè)相對(duì)以往歷史而言的“斷裂”點(diǎn)。更為重要的是,他們?cè)跒槲覀冋J(rèn)識(shí)和確定臺(tái)灣新世代作家提供了一個(gè)較為明確的自然框架或年齡范圍的同時(shí),為我們提供了一個(gè)可以比照著認(rèn)識(shí)、理解的“近鄰階段”,這使得我們不僅較為容易地把臺(tái)灣新世代與前行代在自然屬性上區(qū)分開(kāi)來(lái),而且較為方便地通過(guò)這種自然的區(qū)別認(rèn)識(shí)到不同世代的社會(huì)文化差別。其次,這些論著在對(duì)臺(tái)灣新世代文學(xué)的界定時(shí)都注意到了它的社會(huì)、文化屬性。在現(xiàn)有的臺(tái)灣新世代文學(xué)的研究論著中,西方學(xué)者,尤其是羅貝爾•埃斯卡皮關(guān)于世代的兩重屬性的觀點(diǎn),被朱雙一、王金城等研究者加以了援用。在他們的論著中,臺(tái)灣新世代不僅僅與作家的年齡有關(guān),而且與重大的社會(huì)歷史性事件相關(guān)。在他們看來(lái),作家的生理年齡對(duì)世代的劃分具有的只是一種表征性意義,作家的社會(huì)屬性對(duì)世代的劃分才具有決定性意義。按照簡(jiǎn)政珍、林燿德的說(shuō)法,臺(tái)灣新世代這一范疇既與時(shí)間范圍有關(guān),又與特有的政治、文化空間有關(guān)。他們強(qiáng)調(diào)指出:“我們所以決定采取1949年出生作為斷代基準(zhǔn),不僅僅為了這一年是中國(guó)分裂悲劇的肇始(我們并不贊同政治的斷代足以完全規(guī)劃文學(xué)、藝術(shù)的遞嬗),也同時(shí)考慮文化生態(tài)和思潮變遷的層面”。
而在朱雙一、孟樊、王金城等人看來(lái),“國(guó)民黨退據(jù)臺(tái)灣”、“釣魚(yú)島事件”、“臺(tái)灣被迫退出聯(lián)合國(guó)”等等都可以作為同一系列的詞語(yǔ)代表一種新的世代開(kāi)始出現(xiàn)于二次大戰(zhàn)后的某個(gè)時(shí)間,而臺(tái)灣極權(quán)政治的崩盤(pán)、“黨禁”和“報(bào)禁”的開(kāi)放、冷戰(zhàn)格局的瓦解等等則都可以作為同一系列的詞語(yǔ)代表一種新的世代的全面崛起于20世紀(jì)80年代的臺(tái)灣文壇的某個(gè)時(shí)間。而無(wú)論是那些影響了他們出生、成長(zhǎng)的重大歷史事件,還是那些影響了他們?cè)谖膲绕鸬闹卮髿v史事件,都使臺(tái)灣新世代作家產(chǎn)生了一種相似的政治觀念、道德理念、情感訴求,感受到參與一種共同命運(yùn)的生命體驗(yàn),從而使他們這一世代具有的這一歷史時(shí)期的社會(huì)文化屬性極大地凸現(xiàn)出來(lái)。迄今為止,臺(tái)灣新世代文學(xué)還沒(méi)有引起海內(nèi)外學(xué)者應(yīng)有的關(guān)注和重視。這一方面是因?yàn)榕_(tái)灣前行代文學(xué),尤其是前行代詩(shī)歌的光芒過(guò)于強(qiáng)大,因而導(dǎo)致了研究者對(duì)臺(tái)灣新世代文學(xué)的有意無(wú)意的忽視有關(guān),另一方面則是因?yàn)榇H關(guān)系常常深深地嵌入政治、經(jīng)濟(jì)、文化關(guān)系之中而不為研究者重視有關(guān)。更進(jìn)一步,我們還會(huì)發(fā)現(xiàn),由于主客觀方面的種種原因,即使在現(xiàn)有的屈指可數(shù)的幾部關(guān)于臺(tái)灣新世代文學(xué)的研究成果中,對(duì)臺(tái)灣新世代文學(xué)的內(nèi)涵與外延的界定也仍然存在著一些問(wèn)題。這其中,最為突出的問(wèn)題是未對(duì)臺(tái)灣新世代文學(xué)的橫向性的空間意義進(jìn)行充分的開(kāi)掘。當(dāng)然,這不是說(shuō)現(xiàn)有的研究者沒(méi)有注意到臺(tái)灣新世代文學(xué)的橫向性的空間性內(nèi)涵。事實(shí)上,受羅貝爾•埃斯卡皮的影響,朱雙一、王金城等研究者都關(guān)注到了臺(tái)灣新世代文學(xué)中的“世代”之內(nèi)的不同“組”之間或者說(shuō)亞世代“群體”之間的關(guān)系。然而,這種關(guān)注仍然是不夠的。這是因?yàn)椋罢咧饕獜牧髋傻囊暯莵?lái)區(qū)分不同的“組”,后者主要以出生年代為依據(jù)來(lái)區(qū)分不同的亞世代“群體”。而我們所要指出的是,亞世代“群體”或者說(shuō)“組”不只指涉新世代中的不同年代出生的群體或不同的流派,還應(yīng)指涉新世代中的不同地理出身和社會(huì)———職業(yè)出身的群體。事實(shí)上,在羅貝爾•埃斯卡皮那里,以作家的地理出身和社會(huì)———職業(yè)出身為依據(jù)劃分世代內(nèi)部的不同的亞世代“群體”,遠(yuǎn)較以出生年代或流派為依據(jù)來(lái)區(qū)分不同的亞世代“群體”顯得更為重要。在他的代表性著作《文學(xué)社會(huì)學(xué)》中,他強(qiáng)調(diào)指出,在作家出身情況的集體性特征研究上面,“出身地點(diǎn)這一資料尤其可供我們研究在法國(guó)最引人注目的巴黎———外省的均勢(shì)問(wèn)題。”
顯然,在羅貝爾•埃斯卡皮這里,地理出身的群體不僅是構(gòu)成一個(gè)世代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是它的主要部分。我們認(rèn)為,認(rèn)識(shí)到這一點(diǎn),必將有利于我們對(duì)臺(tái)灣新世代文學(xué)內(nèi)部橫向性空間關(guān)系的全面揭示和把握。遺憾的是,迄今為止,海內(nèi)外對(duì)臺(tái)灣新世代文學(xué)的研究,不論是對(duì)臺(tái)灣新世代內(nèi)部不同出生年代構(gòu)成的亞群體的文學(xué)的一般性研究,還是對(duì)臺(tái)灣新世代內(nèi)部不同流派構(gòu)成的亞群體中的作家的個(gè)案研究,嚴(yán)格說(shuō)來(lái)都是一種偏離了羅貝爾•埃斯卡皮極為重視的“地理出身和社會(huì)———職業(yè)出身”理論的研究,而不是對(duì)不同地理出身和社會(huì)出身的作家加以關(guān)注的研究。也就是說(shuō),這些研究沒(méi)有將臺(tái)灣新世代文學(xué)內(nèi)部的不同地理出身和社會(huì)出身的作家構(gòu)成的亞群體加以辨析和區(qū)別。這種沒(méi)有對(duì)臺(tái)灣新世代內(nèi)部橫向性空間內(nèi)涵加以充分挖掘的研究方法,一方面會(huì)在很大的程度上影響對(duì)臺(tái)灣新世代文學(xué)復(fù)雜性內(nèi)涵和特點(diǎn)的說(shuō)明與闡釋;另一方面,重大的社會(huì)歷史事件帶來(lái)的臺(tái)灣社會(huì)結(jié)構(gòu)變遷也難以得到更為全面的說(shuō)明。例如,眾所周知,20世紀(jì)80年代以來(lái)臺(tái)灣政治、道德、經(jīng)濟(jì)、文化價(jià)值觀的多元化,既與越來(lái)越明顯的代際矛盾與沖突有關(guān),也與相同世代內(nèi)部的不同地理出身的亞群體的矛盾與對(duì)立有關(guān)。只有看到這一點(diǎn),我們才能完整而深刻地說(shuō)明20世紀(jì)80年代以來(lái)臺(tái)灣新世代文學(xué)以及臺(tái)灣社會(huì)結(jié)構(gòu)發(fā)生的質(zhì)的變化。我們將借鑒運(yùn)用羅貝爾•埃斯卡皮極為重視的“地理出身和社會(huì)———職業(yè)出身”理論以及他對(duì)“巴黎———外省”兩個(gè)亞群體加以辨析與區(qū)分的研究方法,對(duì)迄今為止海內(nèi)外沒(méi)有人研究的臺(tái)灣新世代本土詩(shī)人的中國(guó)想象進(jìn)行研究。關(guān)于臺(tái)灣新世代的本土詩(shī)人,我們要加以說(shuō)明和強(qiáng)調(diào)的是:首先,我們所說(shuō)的臺(tái)灣新世代的本土詩(shī)人是指存在于1945年至1979年的時(shí)間范圍內(nèi)的臺(tái)灣新世代作家內(nèi)部中的一個(gè)特殊而又極為重要的亞群體。其次,對(duì)這種特殊而又極為重要的亞群體,我們應(yīng)該從縱向和橫向的多重角度來(lái)審視。從橫向的角度來(lái)審視,臺(tái)灣新世代的本土詩(shī)人與外省詩(shī)人兩個(gè)亞群體是不能截然分開(kāi)來(lái)看待的,它們總是處于一種相互闡釋、相互補(bǔ)充和相互建構(gòu)的關(guān)系之中。我們要完整、深刻地認(rèn)識(shí)與理解臺(tái)灣新世代的本土詩(shī)人的獨(dú)特性,我們就得完整、深刻地說(shuō)明和理解臺(tái)灣新世代的外省詩(shī)人。從縱向的角度來(lái)審視,臺(tái)灣新世代的本土詩(shī)人與前行代詩(shī)人也不能截然分開(kāi)來(lái)看待。我們要完整、深刻地認(rèn)識(shí)與理解臺(tái)灣新世代的本土詩(shī)人的本質(zhì)特性,我們同樣得廣泛而又深刻地認(rèn)識(shí)和理解臺(tái)灣前行代詩(shī)人。再次,通過(guò)上述的從代際關(guān)系的角度對(duì)臺(tái)灣新世代的本土詩(shī)人崛起于與傳統(tǒng)社會(huì)結(jié)構(gòu)截然不同的現(xiàn)代社會(huì)結(jié)構(gòu)之中的描述,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臺(tái)灣新世代的本土詩(shī)人作為一個(gè)問(wèn)題而存在,總的來(lái)說(shuō)是臺(tái)灣現(xiàn)代社會(huì)發(fā)展的產(chǎn)物,或者說(shuō),它作為一個(gè)“現(xiàn)代性”的范疇,是伴隨著臺(tái)灣社會(huì)的高速現(xiàn)代化的進(jìn)程而生成的。
二、本土開(kāi)放性:地理與文化
客觀地說(shuō),詩(shī)人、詩(shī)歌與文化地理的關(guān)系并不是一個(gè)新的話題。然而,在一個(gè)很長(zhǎng)的時(shí)間里,相對(duì)于歷史和時(shí)間,文化地理對(duì)詩(shī)人、詩(shī)歌的影響并沒(méi)有獲得人們應(yīng)有的重視。追根溯源,黑格爾對(duì)這種忽視負(fù)有不可推卸的責(zé)任。黑格爾曾經(jīng)強(qiáng)調(diào)指出:“世界的新與舊,新世界這個(gè)名稱(chēng)之所以發(fā)生,是因?yàn)槊乐藓桶闹薅际窃谕斫沤o我們知道的”。⑦黑格爾的這種忽視空間、重視時(shí)間的現(xiàn)代性觀念對(duì)海峽兩岸的學(xué)者產(chǎn)生了較大的影響。在一個(gè)很長(zhǎng)的時(shí)間里,海峽兩岸的學(xué)者大都是在時(shí)間的現(xiàn)代性范疇中來(lái)討論臺(tái)灣現(xiàn)代詩(shī)的,無(wú)論是面對(duì)紀(jì)弦等現(xiàn)代詩(shī)社詩(shī)人的現(xiàn)代詩(shī),還是面對(duì)覃子豪、余光中、羅門(mén)等藍(lán)星詩(shī)社詩(shī)人的現(xiàn)代詩(shī)和洛夫、痖弦、張默等創(chuàng)世紀(jì)詩(shī)社詩(shī)人的現(xiàn)代詩(shī),海內(nèi)外學(xué)界大都習(xí)慣于使用時(shí)間標(biāo)準(zhǔn)來(lái)打量、評(píng)定。空間和空間寫(xiě)作中蘊(yùn)含的現(xiàn)代性,卻一直沒(méi)有獲得寫(xiě)作者和研究者應(yīng)有的重視。這種忽視,即使在對(duì)20世紀(jì)70年代以來(lái)的新世代詩(shī)歌的研究中也表現(xiàn)得較為突出。而事實(shí)上,20世紀(jì)80年代以來(lái),臺(tái)灣社會(huì)不僅代際之間的矛盾與沖突日趨尖銳,而且相同世代內(nèi)部的不同地理出身的亞群體之間的矛盾與對(duì)立也變得空前的激烈。所謂“本土”與“外省”地理出身的對(duì)峙,在當(dāng)代臺(tái)灣社會(huì)中更是達(dá)到了前所未有的境地。“本土”這一概念,原來(lái)主要有三個(gè)方面的意思:一是指特定地區(qū)人們共同生活的森林、山脈、草原、湖泊、江河等自然環(huán)境以及街衢巷陌、文物古跡、宗教圣地、民俗風(fēng)情等人文環(huán)境;二是指特定地區(qū)人們共同的生產(chǎn)方式、生活方式、法律規(guī)則等制度形態(tài)和政治取向、道德觀念、情感態(tài)度等觀念形態(tài);三是指特定地區(qū)人們共同擁有的種族特征和文化傳統(tǒng)等生理、文化基因。
然而,在當(dāng)代臺(tái)灣社會(huì)思潮中,“本土”這個(gè)原本充滿張力的概念卻逐漸演變?yōu)橐粋€(gè)內(nèi)涵單一的話語(yǔ),甚至異化為一個(gè)充滿排他性的封閉的政治意識(shí)形態(tài)化的術(shù)語(yǔ)。我們之所以這么說(shuō),是因?yàn)楫?dāng)代臺(tái)灣社會(huì)的一些本土論者對(duì)“本土”這一概念進(jìn)行了重新編碼和重新界定,排斥、清除了“本土”這一概念中原來(lái)具有的矛盾性、對(duì)立性、互補(bǔ)性因素,使其變得更為純粹化、封閉化和絕對(duì)化。大致而言,本土論者對(duì)“本土”這一概念的重新編碼和重新界定的工作主要在兩個(gè)方面展開(kāi)。首先,是在強(qiáng)化本土這一概念的同質(zhì)性的同時(shí)泯除了它的異質(zhì)性內(nèi)涵。在本土論者那里,正像臺(tái)灣本土文學(xué)是對(duì)臺(tái)灣鄉(xiāng)土文學(xué)的繼承和發(fā)展一樣,本土這一概念也是對(duì)鄉(xiāng)土這一概念的承接與發(fā)展。然而,如果說(shuō)鄉(xiāng)土這一概念蘊(yùn)含著豐富的階級(jí)性內(nèi)涵,隱含著一種抵抗階級(jí)的宰制與剝削以及對(duì)底層民眾的關(guān)懷的文化內(nèi)涵,那么,臺(tái)灣本土論者則剝離了鄉(xiāng)土這一概念蘊(yùn)含著的這些帶有左翼色彩的思想意義。在他們這里,本土這一概念不再具有階級(jí)批判的進(jìn)步意義,而完全蛻變?yōu)檎位囊庾R(shí)形態(tài)術(shù)語(yǔ)。本土論者在以本土認(rèn)同和命運(yùn)共同體來(lái)代替階級(jí)性差異的同時(shí),也以臺(tái)灣本土人的同質(zhì)性壓抑了臺(tái)灣本土下層民眾的發(fā)聲權(quán)。正如廖咸浩所說(shuō):“鄉(xiāng)土文學(xué)的意識(shí)形態(tài)雖因中國(guó)民族主義影響而有寓言傾向,但其社會(huì)主義色彩,終究能把文學(xué)與文化的視野一定程度聚焦在下層人民身上。然而其后繼者的右翼民族主義傾向,則完全把下層民眾的困苦再寓言化:下層民眾的苦難,乃是臺(tái)灣受外來(lái)政權(quán)支配的苦難,而非階級(jí)的宰制與剝削。階級(jí)議題的‘國(guó)族化’,使得‘人民’淪為了權(quán)力征逐的借口。”⑧其次,是突顯了本土這一概念中的自我與他者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對(duì)立的意義。20世紀(jì)80年代以前,以外省知識(shí)分子為主體所構(gòu)成的前行代勢(shì)力占據(jù)著臺(tái)灣的權(quán)力中心位置,而以本土知識(shí)分子為主體所構(gòu)成的勢(shì)力則一直想從邊緣地帶進(jìn)入權(quán)力中心。從某種程度上說(shuō),后殖民理論恰恰為本土知識(shí)分子為主體所構(gòu)成的勢(shì)力提供了進(jìn)入權(quán)力中心位置的有效的理論武器。借助于后殖民理論,本土論者建構(gòu)了一套自我與他者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對(duì)立的闡釋話語(yǔ)。在這套話語(yǔ)中,“他者”指涉“外來(lái)者”、“殖民者”,“自我”指涉“本土人”、抵抗殖民的勢(shì)力。如此一來(lái),“自我”就先天地具有了一種相對(duì)于“他者”的道德上的優(yōu)勢(shì),它在將本土結(jié)構(gòu)中難以被吸納、化入、整合化的一部分異質(zhì)性存在劃入了“他者”之中的同時(shí),也使原來(lái)占據(jù)權(quán)力中心位置的外省知識(shí)分子在“本土”結(jié)構(gòu)中歷史存在的合理性和現(xiàn)實(shí)存在的合法性受到了質(zhì)疑和顛覆。顯然,在本土論者看來(lái),屬于臺(tái)灣本土人與外省人等其他“他者”的相互間的差異性是確立本土意識(shí)的關(guān)鍵所在。臺(tái)灣本土文化的主體性與獨(dú)特性,正是在與外來(lái)的“他者”文化的參照與比較之中突顯出來(lái)的。應(yīng)該說(shuō),在臺(tái)灣這個(gè)特定的空間里,臺(tái)灣本土文化的主體性與獨(dú)特性確實(shí)是在殖民與反殖民的歷史中逐漸突顯出來(lái)的。在日本殖民統(tǒng)治時(shí)期,臺(tái)灣與祖國(guó)內(nèi)地分隔,臺(tái)灣人的中國(guó)歷史、語(yǔ)言、文化觀念都受到嚴(yán)重的遮蔽,日本殖民者通過(guò)推行種種政治改革及文化政策強(qiáng)化了現(xiàn)代化的臺(tái)灣與鄉(xiāng)土化中國(guó)的對(duì)立。然而,日本殖民者與受其影響的本土論者對(duì)臺(tái)灣主體性與獨(dú)特性歷史的建構(gòu)與敘述并不合乎臺(tái)灣歷史發(fā)展的主流。歷史的事實(shí)是,無(wú)論是在日本殖民時(shí)期,還是在二戰(zhàn)后國(guó)民黨統(tǒng)治時(shí)期,臺(tái)灣社會(huì)的中國(guó)性與本土性并不構(gòu)成相互對(duì)立、相互否定的關(guān)系。對(duì)此,臺(tái)灣學(xué)者黃靜嘉有非常清楚的說(shuō)明:“乙末割臺(tái)雖然使得祖國(guó)大陸及臺(tái)灣暫時(shí)隔離,但兩地之仁人志士仍聲氣相通,而臺(tái)灣殖民地人民之抗?fàn)帲谛再|(zhì)上既為中華民族解放斗爭(zhēng)之一環(huán),自不能不受對(duì)岸祖國(guó)大陸人士或團(tuán)體之影響。”
事實(shí)上,在西方后殖民理論那里,本土這一概念具有非常鮮明的反對(duì)政治、經(jīng)濟(jì)、文化霸權(quán)的意味,隱含著抵抗資本主義的全球化和普遍主義對(duì)于保衛(wèi)地方的主體意識(shí)與獨(dú)特性的意義。然而,臺(tái)灣本土論對(duì)本土的主體意識(shí)與獨(dú)特性的強(qiáng)調(diào),卻并不是針對(duì)西方以及日本等帝國(guó)主義的各種霸權(quán)而言的。這就使得,臺(tái)灣本土論者不僅沒(méi)有理解他們推崇、宣揚(yáng)的抵抗全球化和普遍主義的西方后殖民理論的精髓,而且與這種理論漸行漸遠(yuǎn),走向了與西方反抗霸權(quán)運(yùn)動(dòng)的反面。那么,為何以反二元對(duì)立、反本質(zhì)主義開(kāi)始的臺(tái)灣本土論,最終卻墮入一種西方后殖民理論反對(duì)的二元對(duì)立的本質(zhì)主義的論述框架的怪圈呢?這與日本殖民者對(duì)臺(tái)灣的殖民有著非常重要的關(guān)系。日本殖民者對(duì)臺(tái)灣的殖民的結(jié)果所帶來(lái)的不僅是一種帶有殖民化色彩的較為現(xiàn)代化的經(jīng)濟(jì)市場(chǎng)及其活動(dòng)方式,而且也是一種植根于臺(tái)灣一些人內(nèi)心中的無(wú)法抗拒的殖民文化。這就使得,在后殖民主義語(yǔ)境下,臺(tái)灣的本土化的一種重要涵義理應(yīng)是指臺(tái)灣社會(huì)對(duì)日本殖民主義在政治、經(jīng)濟(jì)、文化等多方面的影響的消除,在精神上重建其主體性。然而,極為吊詭的是,臺(tái)灣的本土化不僅沒(méi)有擺脫這種影響,反而延續(xù)甚至強(qiáng)化了這種影響。對(duì)此,臺(tái)灣學(xué)者陳建忠在《徘徊不去的殖民主義幽靈》一文中批評(píng)道:“日本殖民主義政權(quán)在戰(zhàn)后雖然退出了臺(tái)灣,但是殖民體制在政治、經(jīng)濟(jì)、文化各方面的意識(shí)形態(tài)殘留卻未得到充分的清理;換言之,即未達(dá)意識(shí)形態(tài)上的‘去殖民’狀態(tài)。”⑩而顯而易見(jiàn),如果本土論者不能從精神上擺脫日本殖民者的殖民文化的影響,那么,他們就仍然不能使自己獲得真正完整的主體性。而沒(méi)有獲得完整的主體性的本土論者,建構(gòu)起來(lái)的只可能是一種虛假的排他性的自我認(rèn)同。這種自我認(rèn)同以自我為中心,用本土的標(biāo)準(zhǔn)來(lái)審視和闡釋其他群體。凡是與本土的標(biāo)準(zhǔn)相合乎的便是現(xiàn)代、開(kāi)放、文明的群體,凡是與本土的標(biāo)準(zhǔn)相斥和處于疏離狀態(tài)的便是保守、落后和野蠻的群體。即使在原來(lái)極力倡導(dǎo)本土論的陳芳明看來(lái),這種本土論的極端化、絕對(duì)化生成的文化霸權(quán)對(duì)于構(gòu)建一個(gè)不同族群對(duì)話的場(chǎng)域也是極為不利的。他強(qiáng)調(diào)指出:“綠色執(zhí)政高舉本土意識(shí)的主張時(shí),并未把外省族群視為本土意識(shí)的形塑者的一環(huán)。因此,主張本土之余,無(wú)可避免傷害外省族群的情感與記憶,‘本土’一詞的定義與解釋?zhuān)坪跻驯幻襁M(jìn)黨壟斷。如果繼續(xù)把本土意識(shí)等同于本省人的歷史意識(shí),族群的對(duì)峙與分裂就注定要不止不懈地凌遲臺(tái)灣住民的精神。”瑏瑡在陳芳明看來(lái),如果本土論者把本土論極端化、絕對(duì)化,那么就必然會(huì)引發(fā)臺(tái)灣內(nèi)部不同族群之間嚴(yán)重的矛盾與沖突。因而,只有以開(kāi)放的、進(jìn)步的本土主義論取代本質(zhì)主義的本土論,臺(tái)灣內(nèi)部不同族群之間才能進(jìn)行理性的對(duì)話與溝通,本土論者才能化解而不是催化文化認(rèn)同的危機(jī)。我們認(rèn)為,本土在地理空間上與親切、熟悉的自然環(huán)境有關(guān),在歷史時(shí)間上與悠遠(yuǎn)深長(zhǎng)的文化傳統(tǒng)有關(guān),在語(yǔ)言上與本民族共同、規(guī)范的語(yǔ)言的沿襲相聯(lián)系。在我們看來(lái),只有這樣,本土中的主體才是包含了歷史存在環(huán)節(jié)的主體性存在,而不是將自己從自身的文化、歷史、傳統(tǒng)、自然環(huán)境中割裂出來(lái)的抽象的單面的主體。也只有這樣,本土論才不是一種絕對(duì)化、封閉化的地區(qū)意識(shí),或者說(shuō)不是故步自封地堅(jiān)持一個(gè)民族中的某個(gè)族群的意識(shí),而是在多元開(kāi)放、不斷發(fā)展的動(dòng)態(tài)視域中將母體文化與在地文化交融在一起,使臺(tái)灣島內(nèi)族群間求同存異、相互尊重、平等發(fā)展、共存共榮的本土論。這樣的一種本土論,我們稱(chēng)之為開(kāi)放的、進(jìn)步的本土主義論。有鑒于此,我們把論題中的“臺(tái)灣新世代本土詩(shī)人中”的“本土”理解為一種進(jìn)步、開(kāi)放的本土。本土詩(shī)人的主要內(nèi)涵是:在地理空間上對(duì)臺(tái)灣自然、地理人文環(huán)境的依戀,在歷史時(shí)間上對(duì)悠遠(yuǎn)深長(zhǎng)的文化傳統(tǒng)的承接,在語(yǔ)言上對(duì)本民族共同、規(guī)范的語(yǔ)言的堅(jiān)守。
首先,在地理空間上對(duì)臺(tái)灣自然、地理人文環(huán)境的依戀。對(duì)本土詩(shī)人而言,具有地方感非常重要。所謂地方感,就是本土詩(shī)人與他所居住的臺(tái)灣自然、地理等地方空間發(fā)生聯(lián)系。在本土詩(shī)人這里,地方空間就是他們出生的地方,也是他們的父輩、祖輩出生的地方。因而,通過(guò)經(jīng)驗(yàn)與記憶,本土詩(shī)人可以在這個(gè)穩(wěn)定的地方空間上找到熟悉的地理景觀、穩(wěn)定的自我感與歸屬感。如果說(shuō)在眷村長(zhǎng)大的外省新世代作家對(duì)地方空間的記憶總是與臺(tái)灣的眷村與大陸的故鄉(xiāng)聯(lián)系在一起,作品中總是流露出濃厚的失根的焦慮與苦悶之情;那么,新世代本土詩(shī)人對(duì)地方空間的記憶則總是與熟悉的本土人物、本土地理景觀、本土的民俗相聯(lián)系,作品中總是將地方空間的書(shū)寫(xiě)演繹成為一套知識(shí)系統(tǒng)的介紹。不過(guò),臺(tái)灣這一地方空間既是自然界的產(chǎn)物,又是人類(lèi)社會(huì)實(shí)踐的生成物,在這里各式各樣的自然地理、人文風(fēng)俗等空間糾纏交錯(cuò),建構(gòu)出錯(cuò)綜復(fù)雜的空間形態(tài)。因此,這一地方空間早已經(jīng)變得不再像一些本土論者那樣認(rèn)為的單一化和絕對(duì)化。與此相適應(yīng),在這樣錯(cuò)綜復(fù)雜的空間之中尋求任何單一、排他化的認(rèn)同的企圖,也早已變得不再可能。只要細(xì)加考察,我們就會(huì)發(fā)現(xiàn),外省新世代作家總是將自己的臍帶系住作為自己生命發(fā)源地的大陸與作為自己生命出生、成長(zhǎng)之地的臺(tái)灣兩端。對(duì)于他們而言,兩個(gè)空間緊密相聯(lián)、不可分離,缺一不可。而新世代本土詩(shī)人在描述地方空間的時(shí)候,則總是將地方志與民族的歷史文獻(xiàn)融入詩(shī)歌,使他們的詩(shī)歌不只是關(guān)于地方的知識(shí)系統(tǒng)的介紹,還是對(duì)臺(tái)灣地理、人文歷史演變的知識(shí)譜系的考證。通過(guò)臺(tái)灣與大陸地理、人文歷史社會(huì)的互文性對(duì)照,他們使臺(tái)灣特定的地理、人文景觀成為意蘊(yùn)極為豐富的象征符號(hào)。由此,在新世代本土詩(shī)人這里,臺(tái)灣這一地方空間不再只是本土人物出生、成長(zhǎng)之地,它也是一個(gè)觀看、想象與反思本土人物的母土的一個(gè)最佳的位置,是一個(gè)表達(dá)對(duì)于大陸母土既感到親近又覺(jué)得疏遠(yuǎn),既無(wú)法完全否定又難以完全肯定的矛盾情結(jié)的地方。其次,在歷史時(shí)間上對(duì)悠遠(yuǎn)深長(zhǎng)的文化傳統(tǒng)的承接。本土既與一個(gè)人出生的土地有關(guān),也與傳統(tǒng)相關(guān)的歷史過(guò)去相聯(lián)系。歷史上過(guò)去了的東西,一方面具有流逝性與斷裂性,另一方面又具有連續(xù)性和繼承性。不可否認(rèn),歷史的流逝性與斷裂性總是意味著新的歷史事物的出現(xiàn),然而,無(wú)論歷史上演了多少次重大的斷裂性事件,都不可能完全脫離歷史的連續(xù)性的長(zhǎng)河而發(fā)生。連續(xù)性和斷裂性是同一歷史事件的既相互對(duì)立又相互聯(lián)系的兩個(gè)方面。這意味著,當(dāng)我們談及臺(tái)灣這一地區(qū)的歷史時(shí),不能像一些本土論者那樣只肯定它的斷裂性而否定它的連續(xù)性,或者像一些極端民族主義論者那樣只肯定它的連續(xù)性而否定它的斷裂性。
在經(jīng)歷了后現(xiàn)代主義文學(xué)的無(wú)情顛覆后,臺(tái)灣文學(xué)中的歷史連續(xù)性與統(tǒng)一性已經(jīng)開(kāi)始出現(xiàn)裂縫,脫離了歷史而存在的孤獨(dú)的個(gè)體在歷史與現(xiàn)實(shí)之間漫無(wú)目的地游蕩。與此相呼應(yīng),20世紀(jì)80年代以來(lái)的個(gè)別臺(tái)灣新世代本土詩(shī)人也創(chuàng)作了一些通過(guò)虛無(wú)主義的敘事游戲來(lái)消解和重構(gòu)歷史,以此達(dá)到反抗歷史連續(xù)性與整體性為目的的作品。面對(duì)這種割裂歷史的連續(xù)性與整體性的思潮,大多數(shù)臺(tái)灣新世代本土詩(shī)人對(duì)此進(jìn)行了批判性的反思。臺(tái)灣新世代本土代表性詩(shī)人簡(jiǎn)政珍指出:“新世代詩(shī)人成長(zhǎng)的過(guò)程適逢西方解構(gòu)學(xué)風(fēng)起云涌。臺(tái)灣近年來(lái)有關(guān)比較文學(xué)和文學(xué)理論的探討也使閱讀和解讀沾滿后現(xiàn)代解構(gòu)的‘痕跡’。解構(gòu)學(xué)有關(guān)于‘文字的嬉戲’是否和20、30年前文字的游戲相呼應(yīng),而成為一種風(fēng)尚?所幸,除了一、兩位詩(shī)人外,新世代詩(shī)人大都對(duì)文字嬉戲或文字游戲的理念持保留態(tài)度,意象仍針對(duì)人生思維。”瑏瑢面臨著西方后現(xiàn)代主義文化的強(qiáng)制同化與壓迫,簡(jiǎn)政珍等臺(tái)灣新世代本土詩(shī)人不得不強(qiáng)化他們對(duì)中華歷史文化的記憶,不得不在歷史與現(xiàn)實(shí)的交匯碰撞之中,去探尋自我與中華歷史文化的聯(lián)系。如果說(shuō)在新世代外省詩(shī)人的詩(shī)歌中無(wú)論對(duì)于中國(guó)歷史文化的贊美或反思,都與詩(shī)人的那一份關(guān)乎故鄉(xiāng)、關(guān)乎親人的感情有關(guān),都染上著濃厚的個(gè)人和家族的情感體驗(yàn)的色彩,都是民族歷史命運(yùn)引發(fā)了記憶主體靈魂的震顫和道德關(guān)懷的產(chǎn)物。那么,新世代本土詩(shī)人則常將對(duì)中國(guó)歷史文化情感上的依戀與理性上的思辨結(jié)合在一起,對(duì)本土文化和母土文化進(jìn)行動(dòng)態(tài)、辯證的反思。再次,是在語(yǔ)言上對(duì)本民族共同、規(guī)范的語(yǔ)言的堅(jiān)守。在人類(lèi)文明演進(jìn)的歷程中,語(yǔ)言不僅陪伴著不同時(shí)期的人們渡過(guò)了單調(diào)而又寂寞的漫漫長(zhǎng)夜,而且也成為了民族文化傳承和民族意識(shí)延續(xù)的精神紐帶。眾所周知,占臺(tái)灣人口絕大多數(shù)的閩南人、客家人、外省人,都是從中國(guó)大陸渡海而來(lái)的漢族移民。漢語(yǔ)作為漢族文化的主要載體,既是促使臺(tái)灣地區(qū)之內(nèi)閩南人、客家人、外省人的政治、社會(huì)、經(jīng)濟(jì)生活得以形成的基本手段,也是促成這一地區(qū)民族共同歷史文化賴(lài)以形成的主要構(gòu)筑材料。從歷史的眼光來(lái)看,無(wú)論是受到日本殖民文化還是西方文化的強(qiáng)大沖擊與影響,臺(tái)灣文化都能夠綿延不絕,這既是因?yàn)猷嵆晒εc清政府在臺(tái)灣確立了以中華文化為主體的文化體系,也是因?yàn)樽鳛閭鞒兄腥A文化的載體的漢語(yǔ)的強(qiáng)大的生命力。歷史的事實(shí)說(shuō)明,異族文化對(duì)臺(tái)灣的沖擊、壓制越大,臺(tái)灣民眾堅(jiān)守漢語(yǔ)的決心就越大。在某種程度上說(shuō),漢語(yǔ)既是中華民族文化的傳播媒介,又是中華民族歷史記憶的載體。通過(guò)它,賴(lài)和、楊逵等臺(tái)灣知識(shí)分子可以穿越自我現(xiàn)實(shí)生存的荒誕化和悲劇化的境遇,實(shí)現(xiàn)自我生命的超越。
20世紀(jì)80年代以來(lái),一些本土論者借助地方方言來(lái)反抗作為本民族共同、規(guī)范的語(yǔ)言。這種反抗雖然能夠突顯臺(tái)灣的閩南語(yǔ)、客家語(yǔ)等地方方言的獨(dú)特性,顯示本土論者通過(guò)語(yǔ)言爭(zhēng)奪政治權(quán)力的意圖,卻既對(duì)臺(tái)灣地區(qū)不同族群的交流、融合極為不利,也對(duì)臺(tái)灣地區(qū)歷史文化的傳承極為有害。正因如此,絕大多數(shù)新世代本土詩(shī)人在語(yǔ)言上都秉持了堅(jiān)守本民族共同、規(guī)范的語(yǔ)言的立場(chǎng)。新世代本土代表性詩(shī)人簡(jiǎn)政珍指出:“所謂民族風(fēng)不是以詩(shī)的題材或詩(shī)的主題作為唯一的憑借,而是在詩(shī)表現(xiàn)方式,包括遣字措辭,長(zhǎng)短句的控制,詩(shī)的韻律感,意象的處理方式上讓人覺(jué)得這是中國(guó)人寫(xiě)的。它可能是更像用中文寫(xiě)的詩(shī),而不是西洋句法的中譯,也不是停留于潛意識(shí)的獨(dú)語(yǔ)。不論前一輩或這一代的詩(shī)人,要在詩(shī)作中保持中國(guó)文字的特色已是近十多年來(lái)詩(shī)壇共有的自覺(jué)。”瑏瑣對(duì)于簡(jiǎn)政珍等新世代本土詩(shī)人而言,既然漢文化是臺(tái)灣文化的核心,漢語(yǔ)是臺(tái)灣作家寫(xiě)作所用的共同、規(guī)范的語(yǔ)言,那么,他們的寫(xiě)作就不能不深深地打上民族的烙印,不能不成為民族的價(jià)值觀、審美意識(shí)、文化心理最典型的表征。由此,他們要考慮的不是要不要反抗共同、規(guī)范的民族語(yǔ)言的問(wèn)題,而是要思考如何“在詩(shī)作中保持中國(guó)文字的特色”的問(wèn)題。可以說(shuō),如果抽離了作為共同、規(guī)范的民族語(yǔ)言的漢語(yǔ)言及其漢語(yǔ)言書(shū)寫(xiě),枝繁葉茂的臺(tái)灣古代文學(xué)與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會(huì)變得何等的七零八落!完整的臺(tái)灣歷史文化又會(huì)變得何等的支離破碎!作為整體的臺(tái)灣文學(xué)的發(fā)展、壯大又如何能實(shí)現(xiàn)?就此而論,在詩(shī)作中保持和發(fā)揮中國(guó)文字的特色,對(duì)于簡(jiǎn)政珍等新世代本土詩(shī)人來(lái)說(shuō)不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須的。
三、想象作用力:再現(xiàn)與創(chuàng)造
對(duì)于臺(tái)港澳文學(xué)尤其是臺(tái)灣文學(xué)自塑的中國(guó)形象的研究,既是文學(xué)中的中國(guó)形象研究的開(kāi)創(chuàng)領(lǐng)域,同時(shí)也是最具有現(xiàn)實(shí)意義的研究領(lǐng)域。這是因?yàn)椋芯颗_(tái)灣新詩(shī)中的中國(guó)形象的建構(gòu)與呈現(xiàn),既延伸了文學(xué)中的中國(guó)形象研究的地域空間與審美空間,也有助于更為客觀和理性地審視中國(guó)大陸、臺(tái)灣社會(huì)的政治、經(jīng)濟(jì)、文化交流的歷史和現(xiàn)狀,從而促進(jìn)兩岸同胞的相互了解和認(rèn)知,加強(qiáng)兩岸政治、經(jīng)濟(jì)、文化等方面的聯(lián)系。然而,我們也不得不承認(rèn),迄今為止的臺(tái)灣文學(xué)中的中國(guó)形象研究主要采用的是霍布斯式的再現(xiàn)想象研究模式,而較為忽視薩特式的創(chuàng)造想象模式。這種研究模式大都以題材、主題為限定,同時(shí)將想象看成感覺(jué)表象在心靈中的停留、保持,認(rèn)為臺(tái)灣文學(xué)的中國(guó)形象來(lái)自作家的中國(guó)經(jīng)驗(yàn),既是作為客體的中國(guó)在場(chǎng)弱化后留下的痕跡,也是作家對(duì)自己的中國(guó)經(jīng)驗(yàn)的一種再現(xiàn)與描摹。不可諱言,這種研究強(qiáng)調(diào)了感覺(jué)、知覺(jué)和經(jīng)驗(yàn)對(duì)于臺(tái)灣文學(xué)中的中國(guó)形象生成的重要性,強(qiáng)化了臺(tái)灣文學(xué)中的中國(guó)形象的社會(huì)學(xué)、歷史學(xué)意義。但是,臺(tái)灣作家的感覺(jué)、知覺(jué)和經(jīng)驗(yàn)固然可以生成他們作品中的中國(guó)形象,但研究者把臺(tái)灣文學(xué)中的中國(guó)形象與作家所感知的中國(guó)等同起來(lái),認(rèn)為臺(tái)灣作家的中國(guó)想象只限于被感官所感覺(jué)的中國(guó),則顯然忽視了使對(duì)象虛無(wú)化、非現(xiàn)實(shí)化的薩特式的創(chuàng)造想象。
在西方,盡管人類(lèi)的想象力在文明的積淀之初就開(kāi)始被突顯出來(lái),然而,由于想象被視為與知識(shí)或理智相背離的人的精神直覺(jué)或心理幻覺(jué)的產(chǎn)物,屬于非理性的感性活動(dòng),因而,直到17、18世紀(jì)英國(guó)經(jīng)驗(yàn)主義哲學(xué)興起之前,想象都被柏拉圖等西方哲人看成虛設(shè)的、不真實(shí)的東西,長(zhǎng)期處在理性的壓抑之下的非認(rèn)識(shí)論的或至少是低級(jí)認(rèn)識(shí)形態(tài)的境域。想象地位的大幅度提升,得力于17、18世紀(jì)的培根、霍布斯、休謨等英國(guó)經(jīng)驗(yàn)主義哲學(xué)家。隨著西方哲學(xué)的研究焦點(diǎn)由本體論向認(rèn)識(shí)論的轉(zhuǎn)換,作為人類(lèi)極為重要的認(rèn)識(shí)能力的想象也成為了培根、霍布斯、休謨等英國(guó)經(jīng)驗(yàn)主義哲學(xué)家思考的重要哲學(xué)問(wèn)題。與以前的柏拉圖等西方哲人以及笛卡兒等理性主義者將想象界定在非認(rèn)識(shí)論的或低級(jí)認(rèn)識(shí)形態(tài)的境域的觀點(diǎn)不同,培根、霍布斯、休謨等英國(guó)經(jīng)驗(yàn)主義哲學(xué)家賦予想象以極為重要的地位。英國(guó)經(jīng)驗(yàn)論哲學(xué)的集大成者休謨?cè)诨舨妓沟难芯炕A(chǔ)上對(duì)想象與記憶進(jìn)行了明確的辨析與界定。休謨認(rèn)為,一方面,想象與記憶之間有某種相似性。這種相似性主要表現(xiàn)在它們作為個(gè)體心中的印象都會(huì)以觀念的形態(tài)“復(fù)現(xiàn)”于思想中。“不論記憶的觀念或想象的觀念,不論生動(dòng)的觀念或微弱的觀念,若非有相應(yīng)的印象為它們先行開(kāi)辟道路,都不能出現(xiàn)于心中。”瑏瑤另一方面,想象與記憶之間也有差異性。這種差異性主要表現(xiàn)在它們復(fù)現(xiàn)對(duì)象的方式不同。記憶被“原始印象的次序和形式”所束縛,總是原樣復(fù)現(xiàn)它的對(duì)象;而想象則“不受原始印象的次序和形式的束縛”,可以“自由移置和改變它的觀念”。瑏瑥無(wú)庸諱言,休謨對(duì)這種記憶與想象的同一性與差異性的辨析,從一定程度上推進(jìn)了霍布斯對(duì)想象概念的認(rèn)識(shí)。不過(guò),盡管休謨承認(rèn)想象的能動(dòng)性與自由性,但他與霍布斯一樣,囿于其經(jīng)驗(yàn)論的立場(chǎng),將想象的這種能動(dòng)性與自由性視為有限的,是受到感覺(jué)經(jīng)驗(yàn)的決定的。
與霍布斯、休謨等英國(guó)經(jīng)驗(yàn)主義美學(xué)家將想象看成感覺(jué)表象在心靈中的停留、保持,認(rèn)為想象一定會(huì)受到感覺(jué)經(jīng)驗(yàn)的決定的觀點(diǎn)不同,20世紀(jì)的存在主義哲學(xué)家薩特認(rèn)為,想象是精神的可能性對(duì)現(xiàn)象界的懸浮,是不受制于外在力量和外在目的的精神自我的心靈積極的反思與超越。在薩特看來(lái),想象的第一個(gè)特性在于它的意識(shí)性。想象與實(shí)在之間,構(gòu)成的是一種相互否定的關(guān)系。想象“只能表示意識(shí)與對(duì)象的關(guān)系;換言之,它是指對(duì)象在意識(shí)中得以顯現(xiàn)的某種方式;或者如有人愿意這樣說(shuō)的話,它是意識(shí)使對(duì)象出現(xiàn)在自身之中的某種方法。”瑏瑦這說(shuō)明,想象不是對(duì)現(xiàn)實(shí)存在的感受或印象,想象的意識(shí)只有在對(duì)現(xiàn)實(shí)存在的非對(duì)象化、非現(xiàn)實(shí)化、虛無(wú)化中才能得以呈現(xiàn)。想象的第二個(gè)特性在于它的自由性。在薩特看來(lái),想象不受實(shí)在形象和原始印象的次序和形式的的束縛,“無(wú)論想象怎樣生動(dòng),怎樣令人動(dòng)情或怎樣有力量,它所展示出的對(duì)象都是不存在的。”瑏瑧既然想象意識(shí)不決定于現(xiàn)實(shí)的客體,是非對(duì)象化、非現(xiàn)實(shí)化、虛無(wú)化的,那么,想象所把握的就不是現(xiàn)實(shí)存在而是虛無(wú)。而在薩特看來(lái),想象的虛無(wú)化就意味著個(gè)體對(duì)現(xiàn)實(shí)世界的擺脫,意味著個(gè)體可以超越“自在的存在”成為“自為的存在”。由此,通過(guò)想象,個(gè)體生命實(shí)現(xiàn)了對(duì)過(guò)去和現(xiàn)在的否定,走向?qū)⒗硐搿o(wú)限的東西引入現(xiàn)實(shí)、有限的存在的自由之路。顯然,薩特對(duì)想象的非實(shí)在性和創(chuàng)造性、超越性的闡述帶有較為強(qiáng)烈的主觀化色彩。但正是這種帶有強(qiáng)烈的主觀化色彩的想象論,才對(duì)西方傳統(tǒng)的想象概念進(jìn)行了一次較為堅(jiān)決的思維上的變革。總體看來(lái),西方的想象論受傳統(tǒng)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對(duì)立思維的影響較深。西方古代文明濫觴于愛(ài)琴海區(qū)域,海上貿(mào)易在極大地推進(jìn)了古希臘商業(yè)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同時(shí)也使他們更為尖銳地感受到了人與自然的對(duì)立。從古希臘開(kāi)始,人與自然的對(duì)立就成為西方人認(rèn)識(shí)自然和理解自然的哲學(xué)觀。這種哲學(xué)觀使西方人的想象論以心物二元論為基石,其間或偏重客觀,強(qiáng)調(diào)感覺(jué)、知覺(jué)和經(jīng)驗(yàn)對(duì)想象的決定性作用,或偏重主觀,強(qiáng)調(diào)主觀意識(shí)對(duì)想象的決定性作用。
與西方的想象論不同,就總體的哲學(xué)根源看,天人合一作為中國(guó)這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農(nóng)耕民族的宇宙觀和認(rèn)識(shí)論對(duì)中國(guó)古代的想象論有著決定性的影響。西晉陸機(jī)在《文賦》中所說(shuō)的,“其始也,皆收視聽(tīng),耽收傍訊,精騖八極,心游萬(wàn)仞”,南北朝時(shí)期劉勰在《文心雕龍》中所說(shuō)的“神與物游”,明代的王世貞在《藝苑卮言》中所說(shuō)的“興與境偕”、“神與境會(huì)”、“神與境合”,清代葉燮在《原詩(shī)》中所說(shuō)的“虛實(shí)相成,有無(wú)互立”,就都是由“天人合一”的思想演化而來(lái)的。在他們這里,虛與實(shí)、無(wú)與有在想象活動(dòng)中并不只構(gòu)成截然對(duì)立的關(guān)系,而是構(gòu)成一種既相互對(duì)立,又相互生發(fā)、相互促進(jìn)的關(guān)系。這是因?yàn)椋c西方傳統(tǒng)哲學(xué)將無(wú)視為實(shí)體所占位置或者運(yùn)動(dòng)場(chǎng)域的虛空不一樣,中國(guó)傳統(tǒng)哲學(xué)將無(wú)看成了充滿創(chuàng)造力的氣。由此,無(wú)論是有、實(shí),還是虛、無(wú),都被陸機(jī)、劉勰等人看成了氣,他們?cè)谙胂蟮闹黧w的心中是作為一個(gè)不可分割的整體而存在的。中西想象論的發(fā)展史說(shuō)明,任何只重感性經(jīng)驗(yàn)、感覺(jué)、形象而忽視知性、思想、理念的想象論,都像任何只重知性、思想、理念而忽視感性經(jīng)驗(yàn)、感覺(jué)、形象的想象論一樣,都是極為偏頗的想象論,都無(wú)法從整體上呈現(xiàn)出想象的復(fù)雜特性,都無(wú)法深刻地揭示想象的本質(zhì)特性。這是因?yàn)椋环矫妫藗兊南胂蠡顒?dòng)總是以感性認(rèn)識(shí)為基礎(chǔ)的,離開(kāi)了記憶提供的感性材料,人們的想象路徑就會(huì)變得極為狹窄、怪誕;另一方面,人們?cè)谙胂蠡顒?dòng)中所形成的一些形象,又常常不僅是現(xiàn)實(shí)生活中沒(méi)有的和不可能有的,而且也是未來(lái)生活中沒(méi)有的和不可能有的。正是在這個(gè)意義上,在眾多的關(guān)于想象的定義中,我們?cè)谘芯啃率来就猎?shī)人的中國(guó)想象時(shí)基本上認(rèn)同和采納的是下面這一定義:“人們?cè)谏顚?shí)踐中,不僅能感知當(dāng)時(shí)作用于自己感覺(jué)器的事物,不僅能回憶起當(dāng)時(shí)不在眼前而過(guò)去卻經(jīng)歷過(guò)的事物,而且還能夠在自己已有的知識(shí)經(jīng)驗(yàn)的基礎(chǔ)上,在頭腦中構(gòu)成自己從未經(jīng)歷過(guò)的事物的新形象。這種在頭腦中創(chuàng)造新事物的形象,或者根據(jù)口頭語(yǔ)言或文字的描述形成相應(yīng)事物的形象的認(rèn)識(shí)活動(dòng),叫做想象。”
我們認(rèn)為,這種對(duì)想象的定義,既揭示了想象包含的感性經(jīng)驗(yàn)、感覺(jué)、形象等層面的意義,也展現(xiàn)了想象蘊(yùn)含的知性、思想、理念等層面的意義。我們?cè)谘芯啃率来就猎?shī)人的中國(guó)想象時(shí)對(duì)它的認(rèn)同和采納,既可以使臺(tái)灣新世代本土詩(shī)人想象中國(guó)的不同維度獲得全面的呈現(xiàn),也可以使出現(xiàn)了嚴(yán)重的斷裂現(xiàn)象的臺(tái)灣現(xiàn)代詩(shī)研究中的中國(guó)形象變得完整。具體而言,對(duì)這一定義的認(rèn)同和采納意味著我們?cè)谘芯啃率来就猎?shī)人的中國(guó)想象時(shí)要注意以下幾個(gè)問(wèn)題:其一,在方法上注意對(duì)感性的、經(jīng)驗(yàn)的中國(guó)與知性的、理念的中國(guó)形象進(jìn)行多維的闡釋。在臺(tái)灣新世代本土詩(shī)人對(duì)中國(guó)的想象中,感性的、經(jīng)驗(yàn)的中國(guó)形象與知性的、理念的中國(guó)形象并不是截然對(duì)立的,而是相生相成、一體兩面的。相對(duì)而言,由于臺(tái)灣新世代本土詩(shī)人是在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的臺(tái)灣出生和成長(zhǎng)的,較為缺乏對(duì)中國(guó)大陸的感性認(rèn)識(shí)。因而,較之現(xiàn)實(shí)的中國(guó),他們有時(shí)更愛(ài)知性的、理念的中國(guó)。當(dāng)然,這并不是說(shuō)臺(tái)灣新世代本土詩(shī)人對(duì)中國(guó)的想象中缺乏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性與創(chuàng)作者的經(jīng)驗(yàn)性。事實(shí)上,隨著兩岸關(guān)系的日趨開(kāi)放、緩和,許多臺(tái)灣新世代本土詩(shī)人都積累了到中國(guó)大陸生活、游歷的經(jīng)驗(yàn),這使得他們?cè)S多關(guān)于中國(guó)大陸的詩(shī)歌都不可避免地染上著濃厚的中國(guó)大陸的經(jīng)驗(yàn)色彩。在探尋臺(tái)灣新世代本土詩(shī)人對(duì)中國(guó)的想象時(shí),不僅要注意他們?cè)姼柚械母行缘摹⒔?jīng)驗(yàn)的中國(guó)形象,也要注重他們?cè)姼柚械闹缘摹⒗砟畹闹袊?guó)形象;既要注意他們對(duì)特殊的歷史的中國(guó)空間的想象,也要注意他們對(duì)抽象的、超歷史的中國(guó)空間的想象。其二,在闡述范圍上注意對(duì)烏托邦化與意識(shí)形態(tài)化、政治性與文化性的中國(guó)形象進(jìn)行多元的闡釋。長(zhǎng)期以來(lái),海內(nèi)外學(xué)者較為注重對(duì)當(dāng)代臺(tái)灣本土詩(shī)人的“本土意識(shí)”以及“西方意識(shí)”的研究,對(duì)當(dāng)代臺(tái)灣本土詩(shī)人既接受又抵制西方文化,既疏離又重構(gòu)中華族裔意識(shí)的復(fù)雜性沒(méi)有給予充分的重視。事實(shí)上,在臺(tái)灣新世代本土詩(shī)人的詩(shī)中,作為一個(gè)“想象的共同體”,政治的中國(guó)和文化的中國(guó)常常存在著一種較為復(fù)雜的關(guān)系。如果說(shuō)政治的中國(guó)總是由地理空間、政治主權(quán)來(lái)定義的,那么,文化的中國(guó)就總是以文化和語(yǔ)言來(lái)定義的。對(duì)于前者,大多數(shù)臺(tái)灣新世代本土詩(shī)人雖然不像一些臺(tái)灣新世代本土小說(shuō)家那樣持抵制的態(tài)度,但總的來(lái)說(shuō)態(tài)度較為曖昧。而對(duì)于后者,他們則充滿向往之情。其三,在研究思維上注意對(duì)本質(zhì)化、中心化意識(shí)的超越。迄今為止,關(guān)于臺(tái)灣的身份認(rèn)同大致存在著三種本質(zhì)化、中心化的話語(yǔ)。一種是日本人的本質(zhì)化、中心化的殖民話語(yǔ)、一種是中國(guó)大陸的本質(zhì)化、中心化的國(guó)族話語(yǔ),另一種是臺(tái)灣人的本質(zhì)化、中心化的本土化話語(yǔ)。在日本人的本質(zhì)化、中心化的殖民話語(yǔ)中,臺(tái)灣成為了日本殖民主義的一個(gè)理想的模型,以此印證日本對(duì)異國(guó)殖民的合理性;在中國(guó)大陸的本質(zhì)化、中心化的國(guó)族話語(yǔ)中,則體現(xiàn)出一種極為濃厚的以中原統(tǒng)領(lǐng)、輻射邊緣地帶的意識(shí);而在臺(tái)灣人的本質(zhì)化、中心化的本土化話語(yǔ)中,原本屬于邊緣的地域性文學(xué)在將原有的中心驅(qū)逐后成為新的中心,原本文化史敘述中的反本質(zhì)化、反霸權(quán)化話語(yǔ)則成為了新的本質(zhì)化、霸權(quán)化話語(yǔ)。就我們的研究而言,由于臺(tái)灣新世代本土詩(shī)人的身份認(rèn)同具有較為復(fù)雜的特性,他們?cè)姼鑼?duì)中國(guó)的想象也具有較為多元的形態(tài),因而,我們?cè)谔接懪_(tái)灣新世代本土詩(shī)人詩(shī)歌對(duì)中國(guó)的想象時(shí),一定要突破上述三種從意識(shí)形態(tài)出發(fā)對(duì)臺(tái)灣的身份認(rèn)同進(jìn)行本質(zhì)化、中心化的研究范式,堅(jiān)持歷史性、整體性、系統(tǒng)性的研究原則,超越意識(shí)形態(tài)的局限,重返臺(tái)灣新世代本土詩(shī)人的詩(shī)歌現(xiàn)場(chǎng),廓清歷史對(duì)作為研究對(duì)象的他們的詩(shī)歌的復(fù)雜性的遮蔽,使臺(tái)灣新世代本土詩(shī)人對(duì)中國(guó)的想象得到“原生態(tài)”式的還原和更為客觀、辯證的分析。在研究中,我們將時(shí)時(shí)提醒自己,一方面,雖然我們所研究的問(wèn)題與采用的研究方法具有一定的突破性,但無(wú)論如何,這種研究都不可能一勞永逸地完整地揭示臺(tái)灣新世代本土詩(shī)人的身份認(rèn)同和臺(tái)灣新世代本土詩(shī)人詩(shī)歌中的想象,而只能揭示臺(tái)灣新世代本土詩(shī)人的身份認(rèn)同和臺(tái)灣新世代本土詩(shī)人詩(shī)歌中的想象的一個(gè)側(cè)面。另一方面,鑒于臺(tái)灣新世代本土詩(shī)人的中國(guó)想象本身的復(fù)雜性和多元性,我們一定要超越既有的本質(zhì)化、中心化的研究范式,避免以選擇性記憶或選擇性遺忘的方式對(duì)臺(tái)灣新世代本土詩(shī)人詩(shī)歌進(jìn)行主觀化、暴力化的割裂式的處理,而是以定性分析與定量研究、微觀分析和宏觀綜合、內(nèi)部研究與外部研究相結(jié)合的研究方法對(duì)臺(tái)灣新世代詩(shī)歌“為何想象”、“想象什么”、“怎么想象”、“為什么這樣想象”等問(wèn)題進(jìn)行多方位的觀照。
作者:趙小琪 單位:武漢大學(xué)文學(xué)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