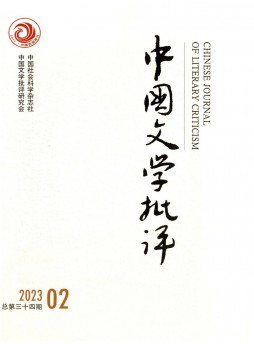文學批評的語言學闡釋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文學批評的語言學闡釋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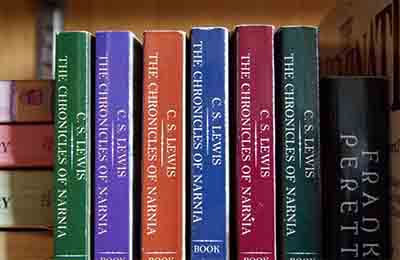
一、人稱代詞的指稱游移
人稱代詞是用來代替人或事物的名稱,其基本用法是指稱明確的所指對象,是指代明確的語言符號。然而,在語言的實際運用中各人稱均有可能不同程度地出現指稱轉移(referencetransfer)現象。南博格提出的延指現象實際上是指從一個話語指稱對象轉移到另一個話語指稱對象的指稱轉移現象。Kuno認為,當說話人將自己認同于話語中所描寫的事件或狀態中的一個參與者時便是移情。按照移情原則中的言語行為移情等級體系(SpeechActEmpathyHier-archy,簡稱SAEH),用公式表示為:SAEH:Speaker>Others,說話人本身總是能夠比別人更容易獲得較高的移情值。相對于其他人稱代詞,第一人稱代詞所指對象能夠獲得更高的移情值。基于這些論說,以下概括性地討論《一間自己的屋子》中第一人稱單數發生指稱游移后的認知與表達效果,而非對各指稱游移現象做窮盡性的描述。作品的開篇有這樣一段,“我利用一個寫小說的人所有的自由與特權,建議講給你們聽我來這里以前兩天的故事———在你們放在我肩上這個繁重的題目以后,我怎樣負了這重任反復地思量它,應用它到我日常生活里去,由生活里尋求這題目的材料。我用不著說明,一切我所要敘述的并非真事。”該部分僅115個字,第一人稱單數出現了7次。這里的第一人稱單數敘事,按照熱奈特對于在敘事者與故事之間關系的分析,屬于同故事(homodiegetic)敘述,即敘事者在故事內,以故事中人物身份講述故事。它表達了作者對于敘事真實性和客觀性的追求。而由于人稱代詞指稱游移現象都不同程度地與移情相關,高頻率地使用第一人稱單數不僅可以讓作者淋漓盡致地抒發感情,還可以抒發強烈的親切感,激發思想與情感的共鳴,讓故事更具認同感。作品的第一章中,作者踏入了牛橋大學。在這里,“我”所遭遇的事情讓內心逐漸失衡。先是“我”穿過一個草坪時被一名警衛憤怒地攔阻,然后去圖書館又遇到一位的老者的擋駕。“我”憤憤然于兩性之間的待遇差別來到女生學院。“我”看到這一切以后想到了很多……”。根據Marmar-idou的觀點,第一人稱單數只有原型性指示,即說話者為指示中心和空間實體。列文森在《語用學》中指出人稱指示就是通過公開的或隱含的人稱代詞把話語中涉及的人或物與說話者、聽話者或第三者聯系起來,表明彼此間的關系。而南博格認為第一人稱單數可作類屬詞(generic),指一類人。伍爾夫使用敘事人“我”,并非作者本人的代稱,而是指代不同歷史時期為婦女運動而努力的幾代人。“我”是歷史進程中的不同女性,具有各個時期女性的個性,是歷史性與差異性相結合的女性主體,也是發展中的女性主體。文中多次出現瑪麗們和“我”之間的對話。“我”與瑪麗•塞頓談論為婦女教育發起募捐活動的婦女們。“我”意識到女性的貧窮除了源于經濟上的依賴以外,主要由于千百年來女性被困于家庭牢籠的社會定位所致。“我”在與瑪麗•卡邁克爾的對話中經常探討女性寫作,“我”看到了女性作家在女性創作這條道路的艱辛,更看到了女性在以自己聲音表達自己的努力。“我”與這些代表各個時期女性的瑪麗們之間的對話,這種不同主體之間的相互關系和相互影響,突顯了主體內涵。人稱代詞在語言的使用中能不同程度地產生指稱游移。伍爾夫在理論文體中引入第一人稱單數自傳式敘述話語方式,增添了理論寫作的主體性、文學性以及抒情性,更加準確有效地表現女性獨特的思想,講述女性的生活經驗,傳達獨立的自我意識,表達旗幟鮮明的女性主義觀點。
二、女性理論闡述中的延指表現
如前所述,語言使用中經常發生指稱轉移。從延指的構成來看,兩種屬性如果以某種方式相互對應,適用于某個域中某物的屬性名稱就有可能被用作另一個域中事物的屬性名稱,而隱喻就是借用屬于一個事物的名稱來表征另一個事物,轉喻的實質是用一個實體來指稱一個與其相關聯的實體。因此,從廣義上講,隱喻指稱和轉喻指稱都隸屬于延指,兩者都是延指的表現形式。伍爾夫在《一間自己的屋子》中以虛構的場所和人物展開了一個開場白,“我不必說明,我將要敘述的情況并不存在:牛橋大學是一種虛構;費恩漢姆也是如此;‘我’不過是代表某個虛構人物的權宜術語。”這里的“牛橋”、“費恩漢姆”是論述展開的地方。伍爾夫用“牛橋大學”這個牛津與劍橋合起來的一個地名,指稱牛津、劍橋之類最高學府,代表男性文化霸權,暗指父權文化統治下的權威價值觀點和價值標準;把“費恩漢姆”轉指剛剛起步的女性教育,隱射女性在社會地位、經濟地位及學術創作等方面所處的貧乏狀態。在此,言者相信自己的指稱是具有關聯性的,聽者可以推理出真正的指稱對象;聽者認為言者的指稱可以通過推理獲知,于是在理解過程中搜尋言者真正的指稱對象,從話語的高度異常中得到明示刺激,從諸多可能的指稱對象中找出具有最佳關聯的一個。在互為顯映的認知語境中,聽者推理出“牛橋大學”是牛津、劍橋之類最高學府的褻稱;“費恩漢姆”指稱女性處境的代表。文中有這樣一段描述:一兩個星期以前,正是絕好的十月天氣,“我”坐在河岸上沉思。人們可以叫“我”瑪麗•貝登,或是瑪麗•塞登,或是瑪麗•卡邁克,或是任何別的喜歡的名字———這完全沒有關系。“我”的思考好似隨波漂流的小魚,它是那么細小,即使漁夫把它撈了上來也會重新將它扔回水里。然而一旦這魚一般的思路在心靈的海洋中暢游,“它立刻會變得十分活躍和重要;它一會跳出水面,一會又沉入水底。它左右穿梭,激起閃亮的浪花,甚至掀起陣陣波瀾。”
按照說話人在默認情況下使用指稱表達時遵循最高可及性原則,“指稱行為在很大程度上依賴語境以及說話人和聽話人的一些推算。”指稱既是交際的客觀指向和交際行為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言者和聽者之間的互動過程。理解話語的字面意義主要取決于話語上下文以及對話雙方的背景知識和相互知識。這里的“瑪麗”是一個完全女性化的名字,它體現了作者渴望表達女性心聲的強烈愿望;而“瑪麗”不確定的姓氏又表明文中的“我”代表著全體女性的集合或各具差異性和主體性的多個個體。文中關于思想的比喻,暗指父權制社會對女性的思想的壓抑與排斥,形象再現了“我”的思考過程,充分顯示了思想的力量。文中的“我”在查找書架上的歷史書時發現英國的歷史就是男性家系的歷史。“我”困惑的是所有著作中女人的形象是那樣的光彩照人,但現實生活中她們卻是男人的奴隸。于是,讓大家一起假想莎士比亞有一個有特殊天才的妹妹。她和莎士比亞一樣稟賦超群,富于冒險精神和充滿想象力,但是被迫否認自己的天才,保持沉默并屈從整個人生。按照人類認知事物時總是遵循著一定的關聯原則,說話者與聽話者往往以關聯原則為基本準則進行明示和推理,以達到指稱的成功。伍爾夫所選擇的莎士比亞的妹妹這一指稱表達式,讓聽者比較容易地推斷出指稱對象為無數具有文學天份的婦女的不幸命運。一個在16世紀誕生并具有詩歌天賦的女人注定是個不幸的女人,隨時都要迎接呼嘯而來的嘲諷和打擊。婦女在歷史上的從屬地位是嚴重阻礙女性文學發展的主要因素。當然,由于作者所處的社會男女極不平等,女性只能在家相夫教子,操持家務,“房間”里的女性是籠中之鳥。另外,在經歷了戰爭之后,作者身體和心靈都受到了創傷,想尋求庇護之所,“房間”指稱的對象轉移為“避難所”。由此看來,“房間”指稱的既是物質和心理的雙重空間,即“圣所”,也是“牢籠”之所和“避難所”。作品中這種延后的解釋是指稱發生轉移的結果,即從一個話語指稱對象轉移到另一個話語指稱對象。“房間”一詞反映了作者復雜的情感,特別是愛恨參半的情結,展示了作者高度的機智和豐富的想象力,也體現了作品的深度和魅力。
基于傳統指稱理論對《一間自己的房間》中的指稱表達式和延指現象背后的語用認知機制進行探討,表明延指既是一種語言現象,也是一種語用現象,它顯示了詞匯、結構和語用信息之間的相互作用。伍爾夫在《一間自己的房間》中運用假設式推理和隱喻的手法,建構了一個既各有含義,又相互發生作用、彼此豐富所指的延指網絡。她的這些富于聯想和意蘊的文字充分揭示了女性主義思想的深宏主題,讓作品耐人尋味、啟人睿智。文學研究離不開揭示語言表現手段的語言學。語言學方法進行文學批評可以了解一部作品的風格特點和主題思想,同時,文學批評也拓寬了語言學的應用領域和范圍。
作者:曾欣悅章力單位:湖南女子學院教授湖南工業大學講師